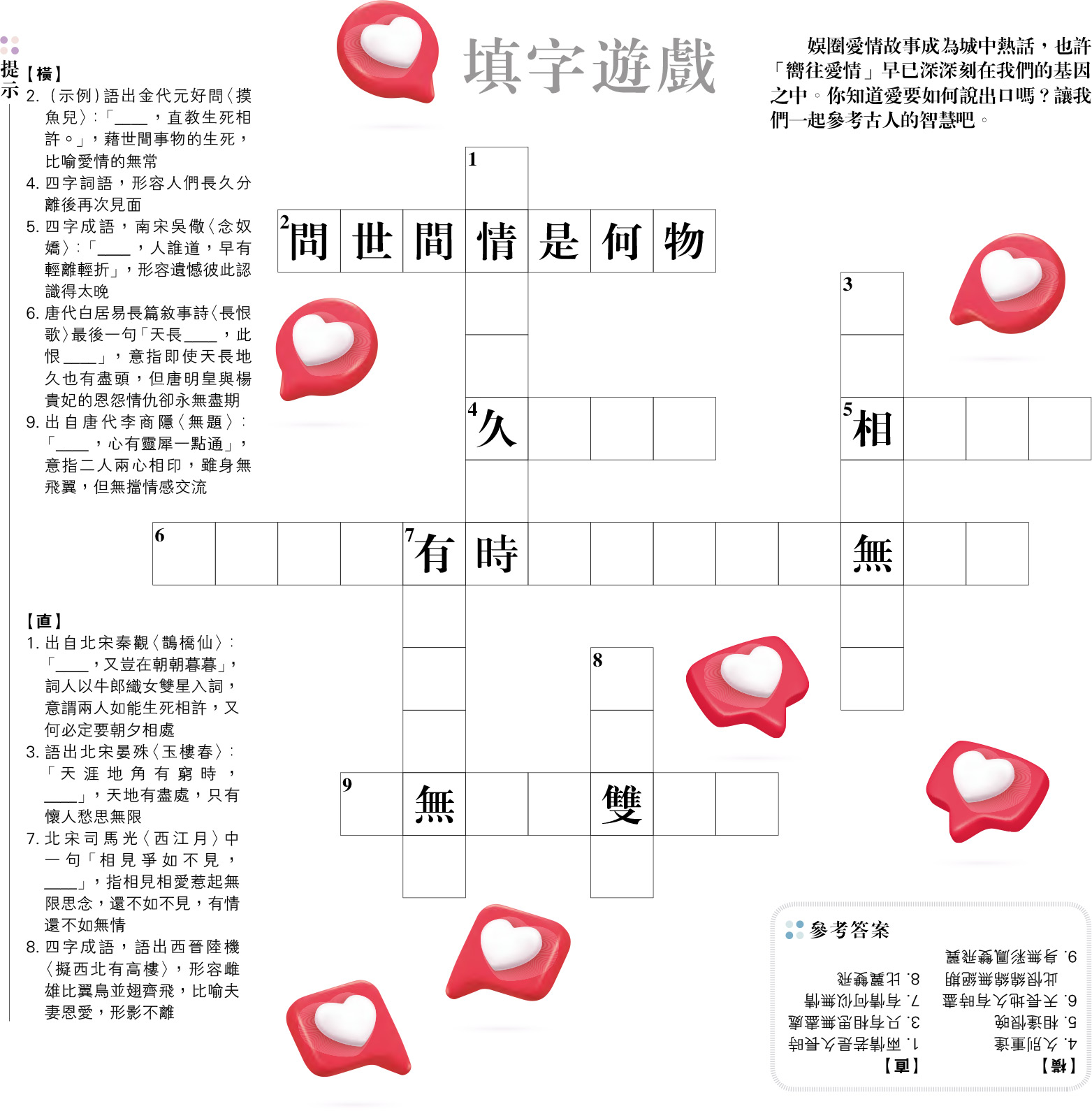視聽之娛:小丑和阿瑟,命運誰關心?——《小丑:雙瘋》
【明報專訊】《小丑:雙瘋》(Joker: Folie à Deux,2024)尚未上映時,不少觀眾嘲笑香港譯名音近「傷風」,上映後大家都彷彿真的害了一場病:網上先有大量措辭激烈的負評,大罵導演玩弄題材、出賣觀眾,票房也確實欠佳;不久出現多篇深入評論,析述導演是如何破格,觀眾的反應正是導演所欲批判者云云。雙方皆陷入瘋狂,筆戰不絕,風潮值得研究。
是「小丑」,亦是「阿瑟」
杜德菲力斯(Todd Phillips)執導的《Joker小丑》(Joker,2019)原來已面世5年,但這部話題作一直沒有離開影迷視線。改編自《蝙蝠俠》經典反派的故事,卻又刻意偏離漫畫設定,重新想像人物,回應這幾年環球政治動盪、貧富差距擴大、集體崇拜瘋狂政客和偶像的真實世情,加上殘破又濃艷的視覺風格,深受觀眾讚賞,甚至出乎意料地贏得威尼斯電影節最高榮譽的「金獅獎」。儘管電影不時遭揶揄照搬馬田史高西斯(Martin Scorsese)傑作《喜劇之王》(The King of Comedy,1982)的意念和情節,場面調度亦不算極高明,影迷還是評價甚高,票房也大收。
上集主角阿瑟(Arthur)受盡冷眼,在人生泥沼中發狂反擊,殺害了幾個欺凌者,化身反社會的「小丑」意外獲群眾支持,被捕入獄激起街頭騷亂。今集延續傳奇,本以為會寫小丑怎樣連結獄外亂世,繼續向無情社會反擊,最終成為混亂(chaos)的化身。可是觀眾期望落空,電影大量運用歌舞片手法呈現阿瑟的幻想(或精神分裂的幻象),大半部戲都像監獄劇和法庭劇的發展,缺少或火爆或狂亂的感官刺激,不易為主流觀眾接受。Lady Gaga飾演的「小丑女」,也和漫畫原作的設定極為不同,她利用阿瑟的錯愛,更令漫畫迷大惑不解。
可是後來不少評論指出,上集已強調這非漫畫中的小丑,是「Joker」而非「The Joker」,借題發揮甚至反轉原作,是文學改編廣受接納的創作精神,今集再行顛覆,不應視為背叛觀眾。事實上,導演想發掘的是「阿瑟」這個悲劇人物的內心世界,他想當笑匠固然具喜劇色彩,但長期飽受壓抑,其後選擇在鎂光燈下發狂反撲,無意中成為受群眾吹捧的「反英雄」,卻又因此困在牢獄兼困於盲從者的思想牢籠。人人只關心「小丑」,無人再理會「阿瑟」,伴隨他只有誤解、暴力和孤獨,這才是終極的悲劇所在。
審視角度決定共鳴或誤解
到底阿瑟真的是精神錯亂,或是沉溺幻想,以此為藉口殺人?在死刑(也包括網絡上的「社會性死亡」)和無罪(甚至被推舉為無政府主義象徵)之間,社會除了極端的二元對立,還擁有多元思想及調和紛爭的空間嗎?說到底,影迷喜歡《Joker小丑》,是因故事反映了當前社會的沉痾,抑或主角反社會的態度,可讓他們藉銀幕暴力發泄?
喜愛荷李活黃金時代的觀眾一頭栽進歌舞片的燦爛世界,忘卻現實煩惱,而片商販賣歌舞片的大喜大樂,麻醉觀眾徹底醒覺的抗力,兩方的拉扯與同流,彷彿醫學術語「Folie à Deux」(共生性妄想症),是共享的妄念與瘋狂。導演採用歌舞片的形式拍攝,正是有同樣的諷刺︰阿瑟的錯覺,觀眾的幻想,同樣源於對社會的不滿,但毁滅世界的欲望不過如歌舞表演般純屬虛構;然而不成熟的妄想集體爆發,就會像片末般引出真正邪惡無序的小丑出場,最後全世界一起遭殃。
《雙瘋》批評媒體嗜血、群眾跟風、社會缺愛的用心,仔細分析起來固然有深意。但觀眾不賣帳,是單純因為不自覺被導演諷刺到而下意識地反抗,還是不認同導演的顛覆精神?運用歌舞片手法諷刺,Lady Gaga的歌藝毋庸置疑,複製經典電影場面也增加了文本深度,但整體歌舞編排單調乏味,節奏拖宕,未能增加觀眾對角色的了解。導演認定大眾只期待Joker,無人關心Arthur,也頗有誤讀和錯判成分——故事強調「There Is No Joker」,但說「There Is No Arthur」也同樣成立。上集之成功,來自現實世界的共鳴跟《喜劇之王》之啟發,更甚於對阿瑟的描寫和創造,觀眾不關心角色,未必是嗜血和冷漠,而是角色不夠紮實,未有足夠獨立性而已。不知你對《雙瘋》又有何解讀?
陳廣隆
(中文教師,影評人,「香港粵語片研究會」及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」成員。著有《誰是金庸小說武功第一人?》)
文:陳廣隆
圖:華納兄弟影片公司提供
(本網發表的作品若提出批評,旨在指出相關制度、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,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,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,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、不滿或敵意。)
[語文同樂 第728期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