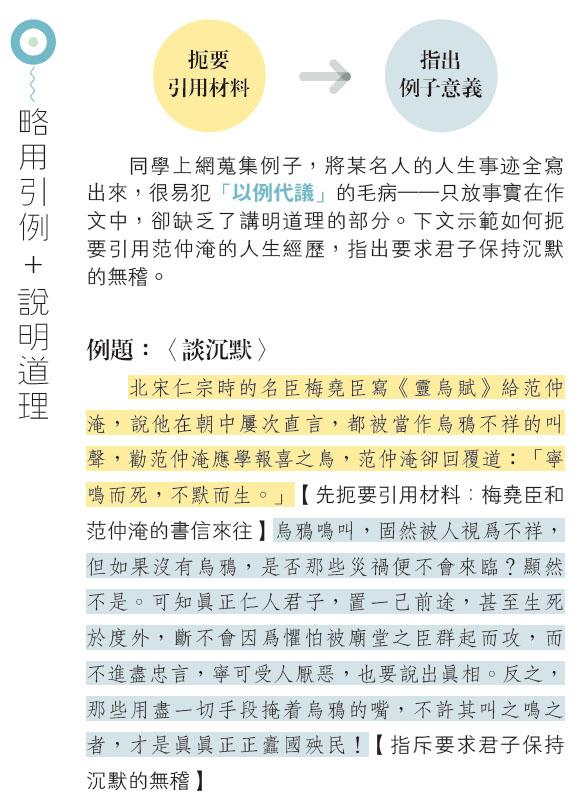書與人生:漂流港青寫故里 既是城市也是鄉土
【明報專訊】蘇朗欣形容自己討厭讀書,轉念一想,又補充,她並不是討厭汲取知識,而是無法接受在課時固定的校園環境裏上課,這讓她很不自在。於是中五時,由於學校不容許她退掉選修科,蘇朗欣決定退學,轉讀夜校,但她依舊討厭那個教室的場景:「心情好的話,我就會(到夜校課室)拍卡簽到,然後溜到圖書館看書,心情不好就直接逃課,卡也不拍。」
愛寫作不愛讀書 獲資助出版成書
逃課不是為了叛逆,只是想這樣做,對蘇朗欣來說,創作也是想做就做的事,是她恰好擁有的謀生技能,起初當然是出於對文字的喜愛,但放置的心力和時間漸多,就變成一項無法輕易割捨的投資,否則就會虧本。《水葬》的前身是幾篇有關新界東北的短篇小說,為了獲得出版經費,蘇朗欣參加了2018年文藝復興基金會舉辦的創作夏令營,這幾篇小說的雛形被導師批評為「只係一啲好似小說嘅嘢」,令她頗為失落,於是用兩晚構思了《水葬》的故事,最終獲得了基金會資助,得以出版成書。
小說斷斷續續寫了兩年,支撐蘇朗欣完成作品的,固然源於對這個故事的喜愛,更是因為:「資助的錢已經領了,無論如何都要寫完。」
《水葬》以多年前一宗發生在新界的無頭女屍案作藍本,以男女主角葉生與夫人各自的家庭故事,牽引出土地發展議題,以及圍繞其中的人性陰暗。一些評論視《水葬》為時代隱喻,寫政治,也寫歷史,但蘇朗欣更願意稱之為愛情故事,比起政局權勢,她更想聚焦一對戀人、一個家庭,甚至只是單純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壓迫和權力利害。她認為文學作品來來去去,描述的其實都是相同的人性,相同的事情,時代背景只是故事的變數,也因為所處的時空不同,人物的選擇亦有差異,當下的我們才有繼續書寫的意義。因此,她的小說從來都不強求反映政治,寫得精彩好看,才是重點。在《水葬》正式出版前,蘇朗欣發表了幾篇與社會運動相關的短篇小說,引來不少討論,例如〈蒜泥白肉〉寫一個「藍絲」母親與被控告暴動罪的兒子;〈水與灰燼〉寫理大圍城事件,都探討了在相異的政治光譜下,親密關係的雙方要如何自處。有人問蘇朗欣,她在作品中對持建制立場的人物,到底是同情還是批判,但她每次都堅拒評論,「小說的目的是呈現,你的立場不同,從中看的東西就會不同」。
「炒散」經歷開拓眼界
說回那幾篇「好似小說嘅嘢」,蘇朗欣如今回看舊作,當然自覺不足,但這也讓她思考:到底什麼才是小說,或者說,怎樣的作品才算是那名導師心中的文學小說呢。在逃掉夜校課堂、溜到圖書館看書的日子裏,蘇朗欣更愛讀流行小說或作品,包括日本輕小說和各類風格的漫畫──如果現在有半小時的空閒,在閱讀文學小說和連看8集《天竺鼠車車》動畫之間,她毫不猶豫選擇了後者。
除了中學時偶然翻到的劉以鬯,蘇朗欣甚少閱讀香港文學作品,她更喜愛外國的小說,例如美國作家沙林傑(J.D. Salinger,《麥田捕手》作者)、日本的推理小說。直至大學時取得第一項文學獎,蘇朗欣仍然不能篤定「好似小說嘅嘢」與真正小說的差別,「大概是對人物心理描寫得深入些吧」。
雖然中五時選擇退學,在夜校也不見得專注課業,但蘇朗欣仍憑着努力自修,以24分的文憑試成績,考進了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,原因是「當時覺得入不了大學,人生就玩完」。然而畢業後進入社會,又是另一番面貌,她幾乎沒有做過一份全職工作,以各類兼職「炒散」維持生計,當過藝術行政、收銀員、展覽工作人員、拍賣行等等。她解釋,一來兼職比全職自在(但她強調前提是起碼要能養活自己),二來這些五花八門的工作,都能豐富生活經驗,成為小說的素材,這些都是無法透過資料蒐集獲取的。蘇朗欣分享最使她震驚的工作見聞,是在拍賣行工作時,有同事把外賣的鹹魚肉餅飯,倒進估價60萬的青花瓷碗展品裏,捧起來進餐,吃完後把碗清洗,瀝乾,放回原位,「更荒謬的是過了不久,青花瓷碗的主人和一個買家前來檢查,完全沒有發現不對路」。
思鄉眷戀成創作重要的母題
26歲,仍在遷移──蘇朗欣在作者簡介中這樣寫道。2019年頭她以工作假期的形式,到了日本,居住了近半年;2020年的秋天,她又來到了台灣,不斷移動的過程中總是會想到香港。起初她以為東華大學在台北,獲取錄後才知道是在東部的花蓮,接着又以為花蓮在九份附近。親身抵達,一切都不如預期想像。
在花蓮生活,需要適應的事情很多,包括提着大包小包的垃圾追趕街上的垃圾車、晚上8點關門的餐廳、一個小時才有一班通往市區的交通工具,這些難以適應的事情都使她煩躁。從花蓮往台北需要坐近3小時的火車,但這半年間蘇朗欣到了台北3次,原因之一是那座城市聳立高樓,是台灣比較像香港的地方,但總是差一點。
蘇朗欣在散文〈歸程待啟〉中,提到指導教授對她講的一段話:「雖然不是鄉下農村那種鄉土,但香港就是你的鄉土,是你的故里,你人在台灣但心放在香港對不對,你會繼續寫她,這是一個很大的母題。」
像她寫《水葬》,選擇以新界東北為題,既是因為想寫土地議題,也是因為從新聞接觸到,地產商和有權勢的原居民在買賣土地時,各種逼遷的污穢手段,使她感到有書寫下來的必要。而說到底,也就是因為:不服。
// 最令人無能為力的是,不論個人的絕望對世界而言如何不必要,它都是非常真實,不可忽視的,它是扎在體內的一根刺,細得無法拔除,又隱隱作痛。//—— 蘇朗欣《水葬》
文、圖:韓祺疇
[語文同樂 第497期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