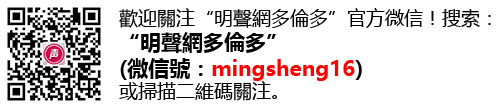閱讀篇章:〈刀工〉徐國能(節錄)
【明報專訊】(1) 常人切割,能夠整齊俐落就算及格,至於刀法則略通砍剁劃拍等常法即已無礙於色味,但要做為廚師,什麼材料用什麼的刀工,卻要花些時間琢磨,不過三五年也可出師,但真正要得到其中精髓,非用一生來追尋,其中還要有名師指點,方可完全。
(2) 當年在健樂園,二廚趙胖子的刀法可算一流,他身廣體盤,膂力驚人,使一柄沉甸甸的馬頭刀,刀腰沾著一抹烏沉的油漬,大骨之類在他手中往往一錘定音,無可置喙,再細小的蔥頭薑絲,也在他肥糯糯的指掌間燦然生華,在刀工裡頗有「通幽」之致,但他自言刀工不及父親,並非謙讓。
(3) 父親用刀不急不徐,但準確無比,手中食物愈切愈小,可還是一絲不苟,直到最後一刀,但這只是入門而已,一般烹飪多是下鍋前即切剁完畢,但有些菜餚需要一體入鍋,待煲熟後才行分割,這種菜最見刀工,其中有許多名堂,如一刀瀝魚脊,只用一劃,即將整條魚骨連魚頭取出,既不扷折,也不留刺,又如分全雞,一罈烏骨雞要在席上半分鐘內分割完畢,罈小雞肥,要能宛轉間肉骨截然,湯水不出,要靠點真工夫。
(4) 父親用刀,除了講究力通腕指、氣貫刃尖與專心致志等泛論之外,對於一把刀的發揮,也有過人之處,如一般人較少用到的後尖,甚至柄梢,父親都能開發其中的奧妙,在許多重要場合派上用場。如前述「一刀瀝魚脊」,厲害的就是刀後尖的運用,料理時後分前挑,一刀兩式,一明一暗,不知其中巧手者真是嘆為觀止,又譬如殺鰻,多數廚子用摔昏法,有時魚未死而腦已碎,血汁一濁,肉質即有變酸硬之虞;但父親的功夫就在刀柄,往魚兩眼間輕輕一頓,再大的魚也立刻翻眼昏厥,再反手一揮,皮骨開矣。
(5) 有回在健樂園,酒餘飯後,論起食道,父親說:古代名庖中,取材調味以殺子入菜的易牙排第一,論刀工則屬莊子筆下的無名庖丁,庖丁善解牛的關鍵是「以神遇而不以目視」,這話說穿了並不特別,只是庖丁對於獸類的筋骨結構比一般人瞭解更多而已,可能是早先研究過牛隻的生理構造,有點像西方文藝復興時代的繪畫,對於人體的肌肉、骨骼瞭解透徹,所以畫作中的肢幹比例、細部表情能更準確而栩栩如生。故這位「科技領先當時一步」的庖丁刀法,恐怕未必有傳說中的神奇。
(6) 自健樂園風流雲散之後,父親絕少下廚,現已茹素多年,再也不碰刀具,連這一手技藝也不肯覓尋傳人,每天但鈔讀陶詩、心經而已,「能吃就好,何必不厭精細」是父親現下的名言。倒是趙胖子南下自立門戶,在高雄闖出了一些名堂。前年趙胖子七十大壽,親披圍裙做了幾樣,自言是晚年的心境神味,父親因病不克前往,命我送對聯一幅,席上展開,寫的是:「心猶未死杯中物,春不能朱鏡裡顏」,趙胖子對龍飛鳳舞的字句飲盡三大白,流下淚來。
(7) 那回飯後,趙胖子微醺之際說出了父親刀藝的來由。
(8) 父親藝業頗有傳奇色彩,父親少年從軍,一直從事文職的工作,據說與寫的一手好字有關,父親字學顏柳正宗,又自出機杼寫成行草,他的解釋是在鄉下寫紅白練出來的,還曾得意的說於老的字也不過如此。來台後,因代步方便,花了參拾元購置二手腳踏車一輛,經常在營區附近老王處修理,這老王不知何許人也,因為來台時遺失了身份證,一直被懷疑是匪諜,謀職無門,只靠修車為業,一年春節,父親在營區寫春聯,因為紙多,一時收不了手多寫了兩幅,無處懸掛,遂轉贈給老王,老王感動之餘,竟說要「切個菜給父親瞧瞧」,硬拉著父親到他的「廚房」,其實只是個違章建築的矮棚,取刀一柄,砧一張,紅白蘿蔔冬筍各一枚,夾心肉一方,二話不說,篤篤篤地開始動手。
(9) 那天黃昏,趙胖子回憶,父親失神落魄回到營區,本來兩人約好要去吃涮羊肉,但父親推說頭痛不去,第二天伙房的老楊神秘兮兮地到處對人說,那個劉少尉真是深藏不露,幾下就把全營的菜都切好,刀法之奇,他幹伙房幾十年也還沒這本領呢!
(10) 這個故事我猜八成是假,不是趙胖子誆我,就是醉後胡言,但向父親求證的結果,父親無可無不可地默認了,但他意味深長地說:「子獨不見貍牲乎,東西跳梁,不避高下,中於機辟,死於網罟……」
(11) 我不明白他們在說什麼。
(12) 父親一生失意,經營事業幾度成敗,其中尤以健樂園的轉讓令其最為痛心,那是他一生的冀望所繫,但近來父親對這事卻有了不同的解釋,認為健樂園的失敗反而是他人生境界的一次拓展,是一種福緣。
(13) 早年曾聽父親自論刀法,父親尚在得意之時,說其刀法有三大奧妙,一是意在刀先,要有靈感才好切菜;二是馬步需穩,如此浮沉二力方能施展;三是聽聲辨位,斷定材料的內部結構才好施力。初聽之際,以為父親是武俠小說看多走火入魔了,但親自下廚時才漸漸體會出話中之理。我求學台中之時,經常在一家香港燒臘店中用餐,那香港老闆刀工極好,叉燒肉片薄如信紙,我暗中觀察其用刀,發現他以左手持刀,右手拿菜找錢之時,左手不忘用刀背輕輕在砧板上敲出一種節奏,這是一種不讓靈感「跑調」的方法,而他切菜,雙膝微屈,兩足不丁不八,愈細的刀工,雙胯越開,父親說這是沉氣於踵,使浮力於鋒線的刀法,市井之中,自有奇人,這是不消說的。
(14) 中年以後,父親更執著於刀工的鑽研,此時他最得意的是發現了均勻吐納與刀工的關係,他常對友朋推廣,既可切好菜,又可健好身,但一般人常聞言大笑,多當他是瘋子看待,為此父親受到不少打擊,從此自己默默「練功」,不再對任何人提起這套「切菜內丹」。尤其後來事業失敗,這門絕技也就無疾而終了。
(15) 晚年父親不再提刀,只寫書法,字中一派圓潤祥和,甚至近於綿軟,不像是殺生無數的人所手書,有一回父親擲筆浩嘆:「我的刀法從字中來,還是要回到字裡去」。我仔細回憶父親用刀,並揣摩了他的書法,這才瞭解父親用刀的技藝,「老王」可能是個神靈啟蒙,而真正的老師,恐怕就是那些人生的風霜,與積疊成簍的唐碑晉帖吧!
(16) 父親病後,我們極少閒談,沉默反而成為我們之間相互習慣的一種語言。
(17) 有一次我偶爾說起他用刀之神,希望能喚起他對往日美好的記憶,但父親只平淡地說:「若非我困於刀工,可能早是大廚了,刀工刀工,終究還是個工!」我明白父親的不甘,當時在健樂園,父親似乎只能切菜,我猜他有更多的想望,但都被他那獨步當世的絕藝所埋沒了,如果沒有這項絕藝……無怪乎他發展出各種玄虛刀工理論,其實都是一種情感的轉移而已。
(18) 回想這些年,父親教我寫字,卻不督促我勤練;教我弈棋,卻不鼓勵我晉段;教我廚藝,卻不准我拜師……,讓我在每件事上,都是一個初入門庭的半調子,一個略知一二的旁觀者,最後他寫給我的一張字是「君子不器」,那時秋夜已深,父親望向庭中那株痀瘺老樹,月明星稀,風動鱗甲,久久不能言語。
(19) 如今我幾乎不到廚房,免得一些不必要的感傷,成為一個真正遠庖廚的君子。我重新拾起書本,發現了其中腴沃的另一種滋味,偶爾可以嘗出哪些文章是經過熬燉,哪些詩是快炒而成,有時我甚至猜想,某作者應該嗜辣,如東坡;某個作者可能尚甜,如秦觀;至於父親晚年最敬仰的淵明,執著的一定是一種近於無味的苦;而刀工最好的必屬黃庭堅,因為他的字那麼率真而落拓,因為他的詩,父親晚年鈔了許多。
(20) 我經常思索父親的哲理,但並沒有成為我人生的指導,有時我會沉溺在某種深邃裡而感到迷惘;但有時則在其中,找到一種真正樸實的喜悅與寧靜。
【實戰篇見另文】
作者簡介:徐國能,1973年生於台北市,東海大學中文系、研究所畢業,台灣師大文學博士,現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。興趣廣泛,喜歡閱讀、電影與棋藝,創作新、舊詩與散文。曾獲聯合報文學獎、時報文學獎、教育部文學獎、台灣文學獎、文建會大專文學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等。散文集《第九味》,曾獲2003年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。著有散文集《第九味》、《煮字為藥》、《綠櫻桃》、《寫在課本留白處》、《詩人不在,去抽菸了》。
作者:徐國能
鳴謝:徐國能先生、台灣聯合文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