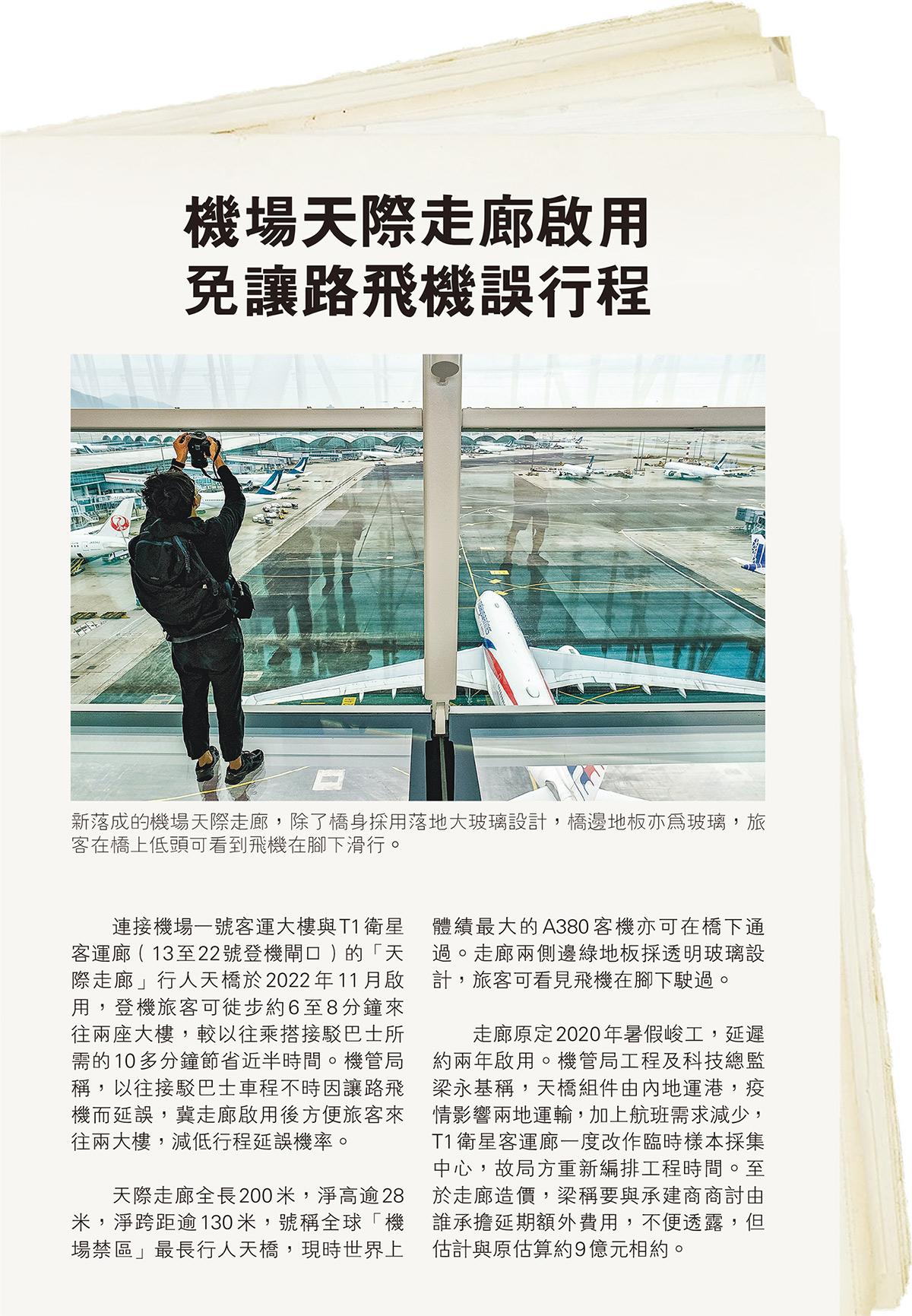詞中物:選擇開窗,讓風景湧入——讀鄭琬融〈在海上〉
【明報專訊】「信任時間、信任變形有它自己的意志,是她的愛。不去懷疑變形的善意,是她的悍烈。去愛,意味着向命運開放,開放一種與異己、與神秘的關係,也開放一種與未來的關係。」評價鄭琬融的詩時,台灣詩人吳俞萱這樣寫道。
獲得第七屆楊牧詩獎、2021年出版的《我與我的幽靈共處一室》,充分展示了詩人鄭琬融的暴力和頹廢,但在字裏行間,又能夠看見作者對世界保留的隱隱的希望。就像詩集中的詩題充滿了像「鬼」、「腐爛」、「末日」、「死去」等字眼,卻同時不乏像〈在海上〉一般充滿溫度的詩作:
傍晚
我把你看作海的時候
海上有煙
風很涼
太陽的血不斷留到你那裡去
我不知道我的船還要多久
才會被岸留滯
我是要走
我想念看見一些不動的樹
上面有鳥
影子被啄得爛爛的
我想念拐個彎就可以碰見你
吃頓熱的
把絞胃的空洞都排出去
但我在海上
這裡沒有花 船長說
這裡最迷人的地方莫過於荒漠
我看出來他早已迷失
他忘記了一點草
他點起了煙
像透了生了我但寡言的父親
我突然想幫他開窗
就像一家人在車上兜風
去哪裡都好那樣
沉入愛海的人
「海」是一個十分寬容的喻體,它能夠比喻的事物實在太豐富,是極為便利的意象。一如物理世界的海,作為喻體,它也有足夠寬廣的胸懷和足夠豐富的形態容納各式各樣的本體。〈在海上〉借敘事者乘船的經歷描繪了一片海景,開篇便把「你」(大概是敘事者的曖昧對象)比作海——對方寬廣,壯闊,有着水體的靈動與溫柔;同時也像世界上所有被煙霧繚繞的海一樣,模糊不定,難以琢磨。沉入愛海中的戀人總是將對方視為生命的重心,於是在第二段,當「我」決心在海上馳行時,太陽的血便不斷向你流去,「我」也不斷向「你」傾注自己的注意力。
但海上的行程畢竟充滿變數,「我」不知何時才會抵達岸邊,何時才能與「你」真正確認關係。正如法國文學家羅蘭.巴特(Roland Barthes)描述,戀情中這種「生怕遇到不測風雲」的焦灼苦苦折磨着「我」,如同絞胃般疼痛。有趣的是,作者在第三、四段不寫海景,反而寫「我」懷念在陸地上行走的日子——陸地上的風景固定且踏實,樹木不動,樹上有清晰可數的鳥,拐個彎就可以碰見「你」,不存在掩目的陰影,一切都清晰可見。可是作者隨即提醒自己現在正身處漂泊不定的海面,像是一錘敲醒自己,意識到自己已經身處愛情的不確定當中。對陸地上的日子愈是懷念,愈突顯出「我」在海上的迷惘和未知,以及因此而生的一點點焦慮。
走筆至此,愛情是焦慮的、不安的、甚至是滿目荒蕪的,若在此處停筆,不僅詩意單薄乏味,其愛情觀也並不立體,但鄭琬融的詩(又或者說愛情)最讓人着迷的地方,就在於它即使飽含萬千悲痛,也無法阻擋人們在當中尋找光之所在的衝動。
滄桑的過來人
所幸這首詩除了「我」和「你」之外,末段還及時出現了第三個角色——船長。若說「我」和「你」是正處於曖昧之甜美酸澀的人,那麼船長則是對愛情已然熟悉,卻在失敗的愛情經歷裏迷失了自己的人。他飽經滄桑的語氣有過來人的無奈,有對愛情悲觀的判定:「這裡沒有花」、「這裡最迷人的地方莫過於荒漠」,短短兩句就道破愛情的虛無,看似有着先知般的見解,但這種否定同時讓他緊緊閉合起來,再也無法看見大海美麗的一面。
愛情,或許正如羅蘭.巴特所說「是以悲劇的形式肯定人生」。於是,在詩的末段,「我」決定一邊承受愛人之苦,一邊告訴船長(同時也在告訴心已枯萎的讀者),或許愛情的遇見,就是選擇把窗子打開,讓風景安靜緩和地湧入,浸潤本已荒蕪的內心。那是對時間之變形的信任,對命運和異己的信任,當心窗打開,那種我們稱之為愛的神秘經驗也會跟隨發生。
■作者簡介
嚴瀚欽
(文學創作班導師,podcast節目《今晚See詩先》主持人之一。著有詩集《碎與拍打之間》(石磬文化,2022)。)
文:嚴瀚欽
圖:KucherAV@iStockphoto
(本刊刊出的文章若提出批評,旨在指出相關制度、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,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,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,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、不滿或敵意。)
[語文同樂 第623期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