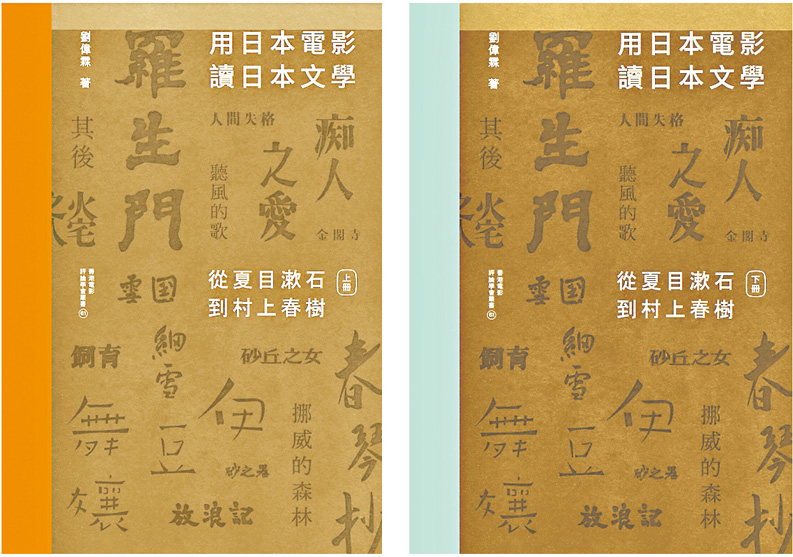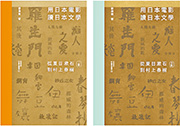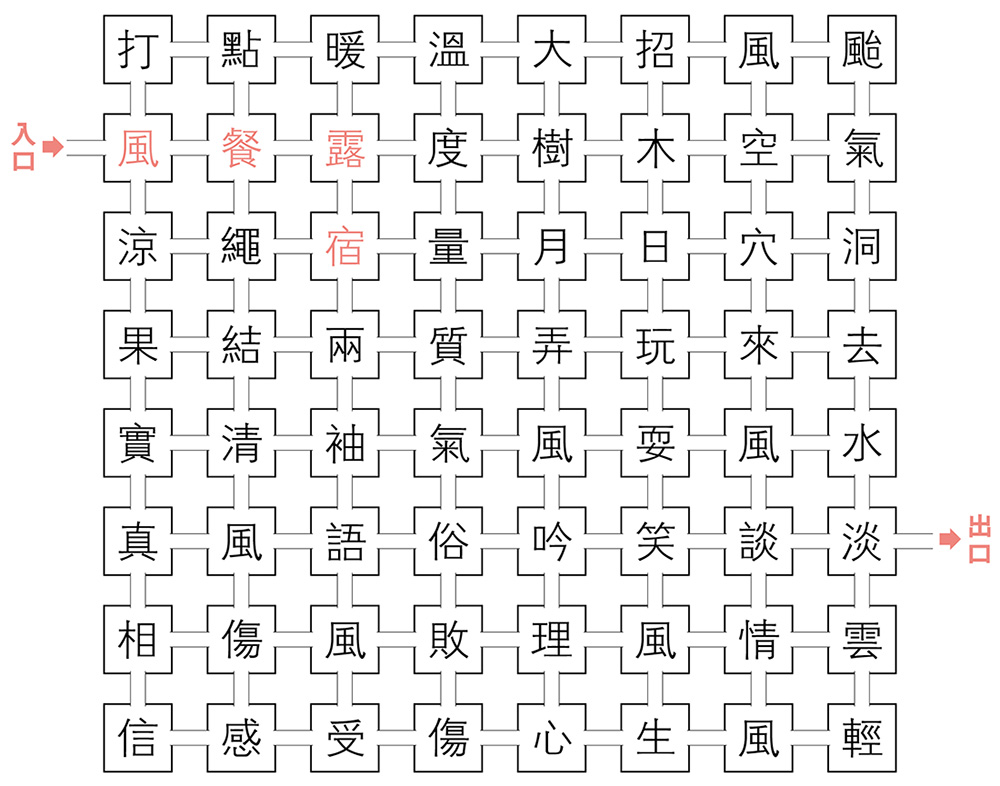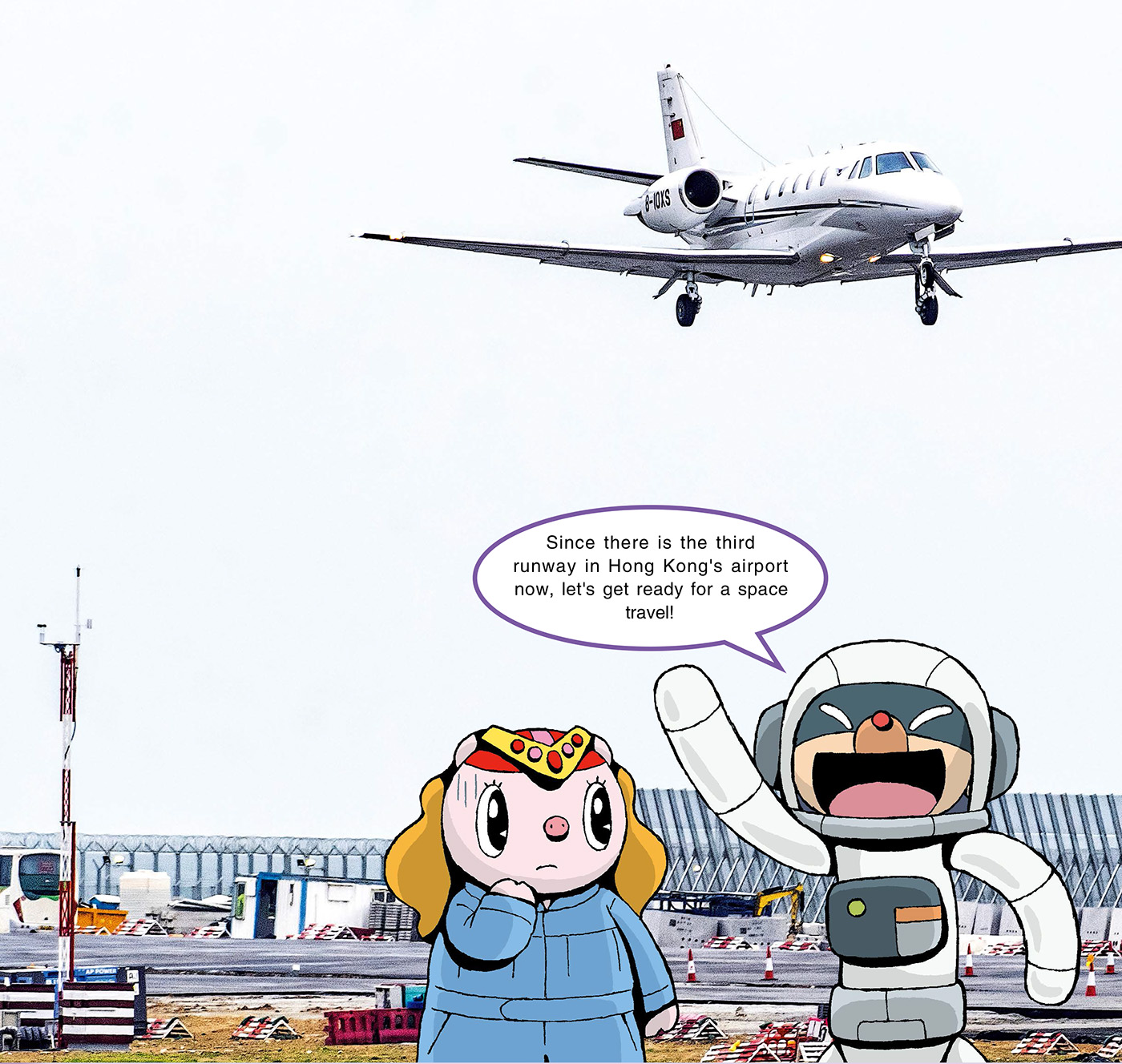視聽之娛:閱讀的濾鏡和透鏡——《用日本電影讀日本文學:從夏目漱石到村上春樹》
【明報專訊】大家對日本文學絕不陌生,每到中文科校本評核的時節,總見同學在捧讀太宰治著名中篇小說《人間失格》(1948),口頭匯報時又以蜷川實花執導的電影海報作簡報插圖,也常見以新海誠動畫《天氣之子》(2019)的小說版為主題,比較文字與影像的差異。日本電影與文學關係千絲萬縷,以「改編」角度探討兩者之間的異同優劣,確是很有意思的題目。
深厚的認識 廣博的研究
若想進深學習,自然得向高手請教。最近劉偉霖撰寫一書兩冊的《用日本電影讀日本文學:從夏目漱石到村上春樹》(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出版),是不可多得的參考書,也是香港鮮見的同類型大部頭著作。劉偉霖是資深影評人,對古典音樂認識深厚,也不時擔任電影字幕翻譯,知道他喜愛日本文學,卻不知原來研究如此廣博。
只要看看目錄,就可體會到作者閱讀有多「廣博」——從夏目漱石到三島由紀夫,由芥川龍之介到村上春樹……7名大作家近百部作品,他都一一細讀並比較歷來各種電影改編細節;至於林芙美子和成瀨巳喜男、山本周五郎和黑澤明等5對合作無間的作家和導演,劉氏也鑽研了他們近40次銀幕創作。除了以上長期的追蹤,他還有20多部「拾遺」,太宰治也在其中,還有吉卜力動畫改編原著,乃至橫溝正史的偵探經典和鈴木光司的恐怖小說。
簡言之,兩冊研究,跨度從百年前的文學巨人,到今天暢銷的流行名家,有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或歐美影展最佳電影的偉大作品,也有娛樂性豐富、時代感強烈的有趣故事,驚人地廣闊,在華語圈中僅見。
獨到之見解 精闢之解讀
廣闊與專深難以兼得,這兩大冊內容異常豐富,但非學術著作,自然不可能每部作品都能就時代背景、美學處理、文化意義等範疇仔細探討,但看作者如何撮要內容、聚焦比較,準確判斷,就見深耕細作的工夫。他的書題定得好︰這是「用」日本電影「讀」日本文學,導演的處理手法就是「濾鏡」,選擇地折射原著的意涵;劉氏的閱讀則是「透鏡」,為讀者聚焦光源,專注其中一個角度。
例如書中討論三島由紀夫的名著《金閣寺》(1956)與導演市川崑改編的《炎上》(1958),劉氏撮寫原著內容和評論電影改編,各只用了不足千字已切中肯綮,他強調「片中很多地方和原著不同,但在此一一列出恐怕意義不大,因為總括來說,編劇已經不是改動或保留原著細節那麼簡單,而是重新建構一個可以拍成電影的劇本」,這種目光已和一般只爭論改編是否符合原著的討論大不相同。劉氏點出:
以第一身敘述而言,《金閣寺》的主觀敘述非常極端,讀者就如進入了溝口的身體,聆聽他異常扭曲的思想,用他過度敏感的眼光去看周遭的世界。即使電影語言有主觀鏡頭及旁述這些第一身敘述的工具,但本片極力避免,旁述更是完全沒有。導演非但不是用電影手法去呈現主觀,反而將主觀變成客觀……不像原著般對金閣有什麼『美之極致』的執念……市川崑不用電影手法進入溝口內心,溝口亦無法向世界表達他的思想,觀眾也無法真正理解溝口的鬱結以及犯案的具體原因……(頁237-239)
短短一段文字,已就作品主題、敘事手法、視角差異,極其扼要地分析。閱讀《金閣寺》原著,讀到諸如「我曾針對一片草葉尖端的銳角長時間思考。說是思考並不恰當……在我不知是生是死的感覺上,就如歌曲副歌般執拗地反覆出現」(黃瀞瑤譯本,頁198)等句子,必可感受到劉氏「極端」、「敏感」等評語之精準。
尤其是粵語長片年代,香港電影不時改編世界名著,但近年是愈來愈少,除了張愛玲和金庸能引起迴響,像不久前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改編余兒小說,評論界也鮮有認真研究文字和影像的差異。最近「電影節發燒友」正舉行「日本文學映畫祭」,選映10多部改編著名日本作家作品的電影,不少都在劉氏的討論範圍,《炎上》也在其中,同學可藉此印證他的分析。同期香港電影資料館也在舉行「舞文弄影——香港電影與文學」節目,精選17部1940年代至近年的電影,以展覽、以專書、以映後談形式細說電影和文學的交匯,同樣值得留意。說不定,將來會出現一部由同學撰寫的《用香港電影讀香港文學》,為我城的文化和藝術研究有更精彩的貢獻。
■陳廣隆 - 中文教師,影評人,「香港粵語片研究會」及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」成員。著有《誰是金庸小說武功第一人?》
文:陳廣隆
圖: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提供
(本網發表的文章若提出批評,旨在指出相關制度、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,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,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,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、不滿或敵意。)
[語文同樂 第740期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