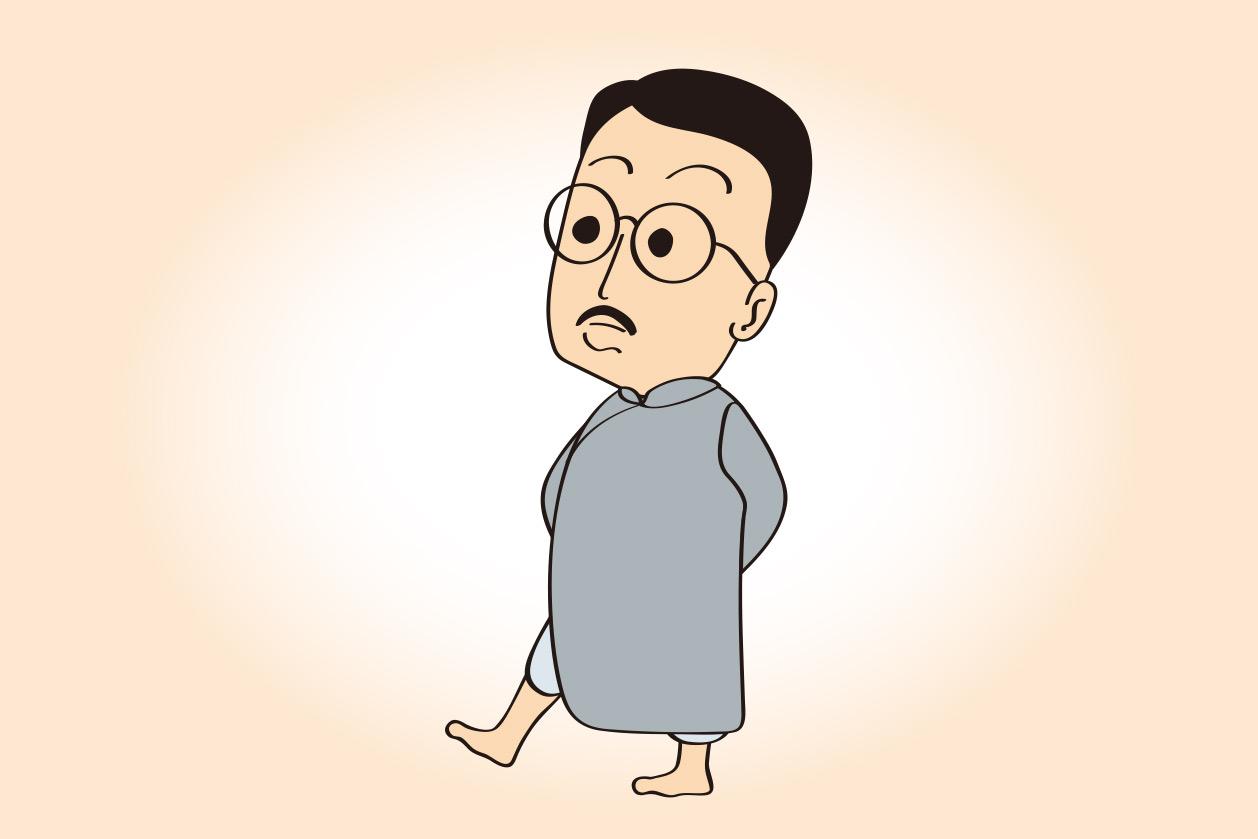潮看文史:捱(ngaai4)冷(laang5)
【明報專訊】俄烏戰爭下能源緊張,歐洲電費升幅以倍計,英國人早前更疑慮冬天要「餓死還是冷死」。對已沒有冬天的我們而言,那不過是遙遠甚至覺得誇張的說法,但在高緯度地區,寒冬從來都是大敵,中原本位的傳統文化也是如此。
溫飽
子曰:「歲寒,然後知松柏之後彫(凋)也。」以冬天喻逆境,是傳統常見修辭。不同於現代擔心「手停口停」,古人關心的除了飽還有溫,《孟子.梁惠王》中仁政應是「七十者衣帛食肉,黎民不飢不寒」,抵冷與飽肚同等高度。在靠穿衣燒炭禦寒的古代,每個寒冬都不易過,就算富庶的宋代,「大雪民多凍死」不算鮮見(見《宋史.五行一下》)。縱使撇除災荒,山西(介子推故鄉)東漢時的冬天寒食之俗(禁止生火一個月)亦「老小不堪,歲多死者」(《後漢書.周舉傳》),可見北方的嚴酷。亦正因重視保暖,養蠶技術早在周代已成熟得絲綢外銷,令古希臘稱中國為「絲國」。
興亡
寒潮這類異常氣候古人會視為亡國之兆,雖在現代人看來不脫迷信色彩,卻非毫無道理:氣候確可改變政權運數,尤其測試管治能力(詳見2017年本欄的〈天災亡國不止是迷信〉)。若撇開人治問題,單看溫度對歷史的影響,現代學者也已研究得不少:長期偏冷之時,政局偏向荒亂,中國四個寒冷期商末周初、漢末魏晉、北宋中至南宋中、明中至清初皆如此。最直觀的理解是天災頻仍危及農產以至人命、游牧民族缺乏水草而南下,外侵內亂此起彼伏,加速衰落皇朝的滅亡。反之氣候溫暖則有利於農耕帝國,漢逐匈奴、唐驅突厥都處於溫暖期,並非單純繫於國人追求的明君。
寒衣
古時冬天之始的十月初一(寒衣節、十月朔),有着授衣開爐的習俗,亦是秋祭大日子,百姓會焚燒象徵綢緞的五色紙以贈逝者,是個求溫的節日。說來諷刺,雖然孟子的藍圖是家家戶戶養蠶取絲以衣帛,實則絲綢技藝高深而矜貴,平民難以求取,穿的一般都是麻料,保暖效能有限,才會以布衣、寒門比喻貧苦出身者。直至宋末南方棉織技術北傳、元明推廣棉樹,方令至今仍是禦寒主力的棉製品普及。物料進步了,偏偏明清面對的是近數千年最冷的小冰河期,災荒遠超前代,棉衣也幫不了多少。到了暖氣處處的現在,似乎終能擺脫衣料的局限——亦正是如此傲慢,才有當今的能源危機。
■延伸閱讀
〈潮看中化:天災亡國 不止是迷信〉
(第264期《語文同樂》,2017年9月22日)
葉雨舟--書呆子一名,喜歡反思中日韓歷史文化的種種,希望東方社會能重拾對東方文化的認識。
文:葉雨舟
圖:路透社
(本刊刊出的文章若提出批評,旨在指出相關制度、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,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,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,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、不滿或敵意。)
[語文同樂 第632期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