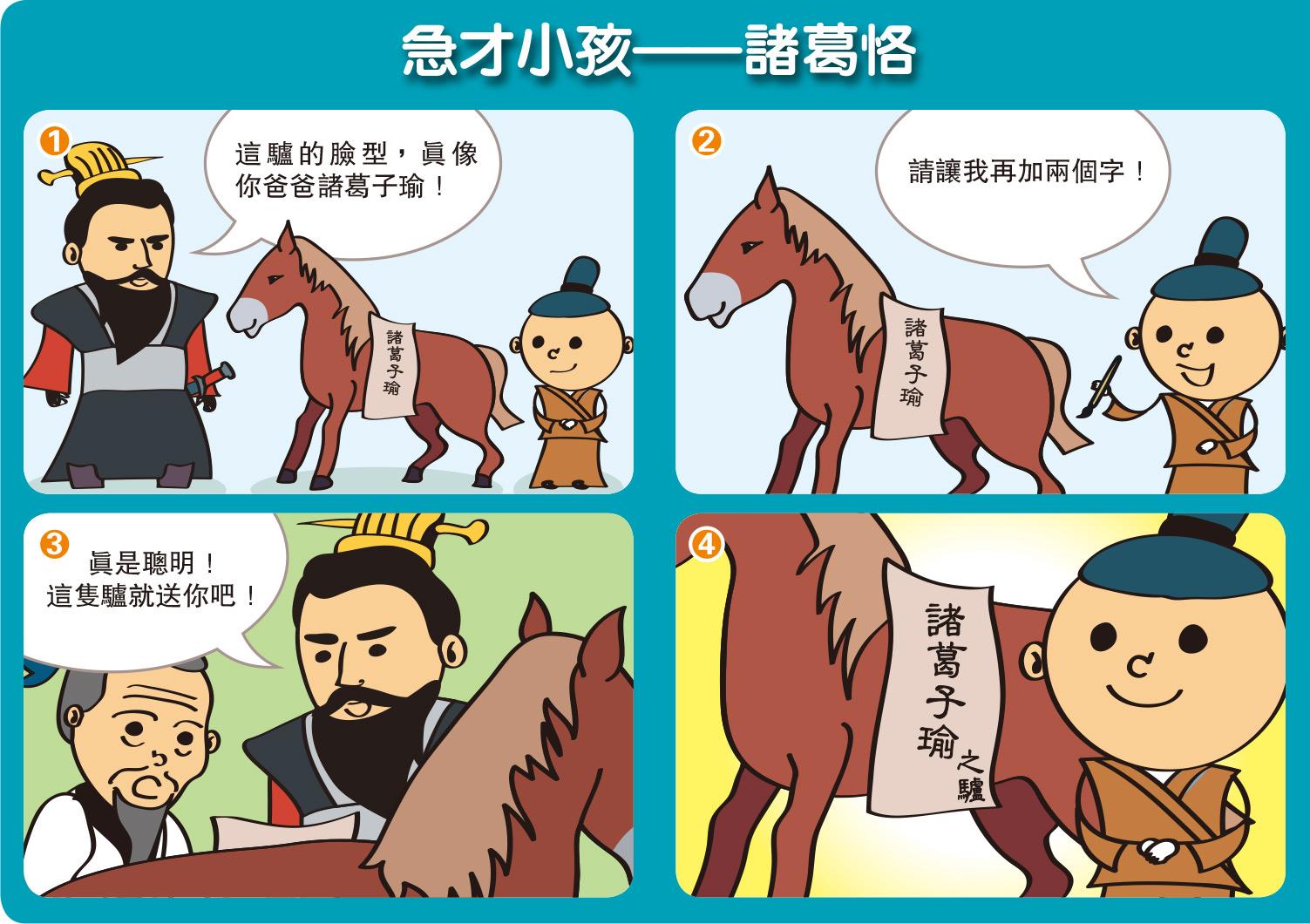字遊打卡:命若浮雲的陶然
【明報專訊】生命是一趟旅程,這個老套的比喻,我想,還是可以用在陶然身上,而他的旅程應該是散漫的,沒有特別要去或不要去的地方。如果可以選擇躺在雲上,他絕對不會乘坐飛機。
《今夜,菜街歌舞沉寂》是香港作家陶然死後出版的散文集,他的好友曹惠民在序言寫道,文章是他生前選訂的。香港文壇朋友認識陶然,大多是因為他繼任劉以鬯接手編輯《香港文學》雜誌,筆者也是這樣認識他的。1943年陶然在印尼萬隆出生,還是16歲年輕小子的他,以華僑身分到北京讀書,豈料遇上1960至70年代社會動盪的日子,回不到父母的身旁,孤身留在北京10多年,與父母一別15年。最後陶然在1973年到香港定居,當報刊編輯,認識各方朋友,發展他的文藝事業。然而,在2019年3月9日,他因感冒引發重病而突然離世。
翻開《今夜,菜街歌舞沉寂》才知道,原來陶然在生前的數年,寫了不少關於自己過往經歷的散文,現在回看是他的回憶錄了。此外,他到過五湖四海,書中寫日本札幌、小樽、神戶;又寫韓國首爾、光州;甚至去過莫斯科、聖彼德堡;還有台北、九份、宜蘭;當然還有不少中國大陸的地方。這本書記錄了他生活過、遊歷過的地方。在〈雪飄札幌〉一文,他這樣寫:「我們並沒有一定目的,隨便走走而已,所以也輕鬆,毫無負擔,其實旅行就應該如此,毫無負擔才好。」讀到這裏,我停了下來,心中感到這不就是他的處世之道嗎?經歷過沉重的歷史、俗世的糾纏,到頭來還是輕身上路。
在這些遊記中,筆者特別喜歡陶然寫帶有個人回憶的地方,尤其是東南亞城市,這些遊記他寫得最好。陶然的散文能寫出一種「浮生」的感覺,就好像電影中的大遠鏡,一個人在無盡的平原上。〈滄海一粟〉寫他少年離開成長的萬隆,乘船到北京的海上旅程,場面有點像李安的電影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,掀起3層樓高的巨浪,然後大海又平靜過來,看到飛魚在跳躍。因為萬隆是山城,當時16歲的陶然對大海的感覺是陌生而震撼的。浮生在世的感覺,或許在甲板凝望黑沉沉的海洋那一刻已經注入他身體中。
陶然的萬隆回憶也有搞笑的一面,畢竟他當時只是少年。我認識的陶然對自己的打扮甚講究,原來他少年時開始追隨潮流,學習當時美國影星占士甸梳「飛仔頭」,結果引起同學大笑,他衝入洗手間把所有髮蠟冲走。他在〈潮流髮型〉寫道,這件童年往事對他影響很大,讓他明白到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潮流打扮。之後無論陶然到了較保守的北京或較開放的香港,潮流變成了他戰戰兢兢的一環。
我之前看過陶然另一篇很好的散文〈別離的故事〉,他回憶起這段少年離鄉的往事,寫道「但在這以前,不知為什麼,我總有個錯覺,以為這不過是一次遠行,去了還會回來。但,我就像隻斷線的風箏,永遠也回不去了。」萬隆他是回不去了,但香港仍是歡迎他。我的手機還存有與他的通訊紀錄,他最後一句跟我說的話是「唔知佢想搞咩」。陶然的漂泊人生,在港式幽默中停止。
黃淑嫻--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、香港作家
文:黃淑嫻
圖:LeeYiuTung@iStockphoto
(本刊刊出的文章若提出批評,旨在指出相關制度、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,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,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,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、不滿或敵意。)
[語文同樂 第618期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