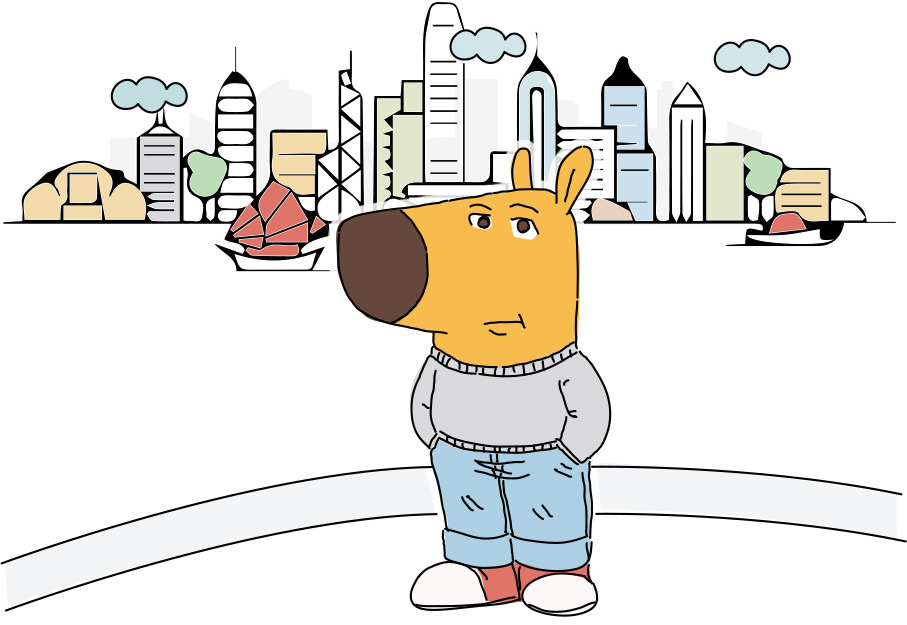名家學堂:連「城」一線:70後的時代記認
【明報專訊】人們常以「00後」、「10後」等方式統稱同一個世代出生的人,並歸納出某些特質。當我們長大後回憶自己的成長經歷,察覺到與同代人有着共通的童年記憶,由此形成了獨特的情感連結。作家張婉雯是《差異與連結——香港七十後作家對談》的對談人之一,她在對談集出版後才讀到其他組別的對談內容,發現那些當時只道是尋常的事物,原來已經成為時代的重要記認。
流行文化:彼此最大公約數
1月舉辦的講座「不期而遇的世代經驗——七十後作家眼中的香港文學及文化」,邀來作家張婉雯和學者張歷君主講,《差異與連結》主編郭詩詠則是主持,3人同是「70後」。郭詩詠認為,以10年作為劃分,或許過於硬性,她解釋同代人如何形成,往往是他們身上曾經歷相似的事件,或者在一些重大事件的當下,不同世代的反應與迴響並不相同,例如3歲的小孩和70歲的老人都曾經歷疫情,他們的記憶和遭遇卻不盡相同,呈現了世代分野。因此郭詩詠認為同代人的形成,是透過歸納重組,尋找他們的「最大公約數」。
流行文化是「最大公約數」之一,張婉雯回憶當年追看的動漫《鐵拳浪子》、收藏的潮流雜誌《amoeba》,原來也影響了其他同代作家的童年。她提到在網絡不發達的年代,紙本雜誌與讀者能建立更緊密的關係,編輯與讀者會互動通信,交流健康知識、日常穿搭建議、感情疑問等,題材也更豐富多元,種種記憶甚至令張婉雯覺得「香港的『70後』可能是最後一代幸運的人」。這些交流在今天則搬到社交平台,便利店的報紙架正逐漸消失,張婉雯仍在思考其中的差異,表面上是接受資訊的渠道轉換了,但會否使資訊變得單一?另一個可見的變化是,由於搜尋器總能精準找出答案,反而失去在書店中迷惘地找書,卻有意外發現的體驗。郭詩詠認為這也是屬於同代人的重要記憶,「(在各組對談裏)不同作家都會提到一些類似的事……例如他們有很大的動力去講述他們在報攤、書店中尋寶的經歷」。
網絡崛起:介乎適應與不適應
時間回到2004年,facebook成立,其後開放給中文世界的用戶,對談集裏不少「70後」作家都有設立作者專頁,並累積數量可觀的追蹤者,例如韓麗珠專頁的追蹤人數已破萬,郭詩詠也在書中打趣道:「『韓麗珠』那個戶口,其實已經跡近,你只要上去『唉』一聲,就已經會有很多讚」;有些作者如小說家謝曉虹則自認「很不適應網絡世界」。20年後,facebook已經不是新鮮事物,掌握「流量密碼」的素人也能輕易獲得過萬讚好,但回到互聯網剛盛行的年代,對寫作者帶來不少的機會和挑戰。
張歷君回看這群「70後」作家成長和活躍的1990年代,冷戰剛結束,全球化和網絡時代來臨,令人們有了自由的「幻覺」,可以隨時與不同地方連結,於是希望做一些非主流的事情,追求古怪,也形成某種共同的特質。當時年輕的作者透過互聯網與更多讀者互動,又尚未受限於演算法,也沒有點擊率的壓力,願意關注獨特議題,交流更為多元。張歷君也提出「70後」作家的夾縫處境,他們比起前輩更願意接觸新科技,但也更難適應重視演算法的facebook。
張婉雯分享一個作者朋友在Threads上做的社會實驗——他嘗試發不同題材的帖文,測試什麼內容可以獲得最多點擊率,結論是:提問哪首廣東歌令你印象最深刻、裝作外地遊客請大家推介美食、分享家庭和成長創傷。張婉雯說演算法令網絡世界變得單一和沉悶,只要掌握關鍵詞就能輕易引起迴響,社交媒體也為作家帶來啟示,「作家自詡為邊緣,但在這個世代好像又無法邊緣。我們如何在自我探索和接觸大眾之間,找到一個平衡?我自己還是未想通透,這可能就是『70後』作家尷尬的處境,『摺』又不是很『摺』,開放也不是很夠開放」。
關注議題:同中有異 異中有同
《差異與連結》一共收錄14名作家的對談,有共同的連結,亦有明確的差異。除了互聯網浪潮,不少作者皆提到2000年代的天星及皇后碼頭保育運動、菜園村事件;再往前推,便回憶到大學校園開放討論的氛圍,如何開啟他們對社會議題的關心。不過啟蒙只是起始,作家對議題的關注,也有細分的傾向,例如張婉雯關注動物權益,不少作品與之相關,寫動物被忽視的處境,也由此觸及人與社區的變化,例如小說〈老貓〉便藉一隻茶餐廳老貓的眼睛,觀察舊區的人情和變遷,同時反思動物與所屬社區的關係。
韓麗珠和謝曉虹都常寫到貓——當然並非為了「流量密碼」。二人風格與張婉雯相異,郭詩詠也在書中的對談裏提到:「因為我們亦有一些同代人,譬如張婉雯或者早期的李維怡,比較傾向現實的寫法。張婉雯一般是不會給貓有任何對白,是現實的貓,會跟現實裏的貓相似,但你們(指韓和謝)的貓是會飛的,會做這樣那樣的事。」這些會飛的貓出現在小說集《雙城辭典》,由韓麗珠和謝曉虹合著,小說被視為魔幻寫實的作品,以許多非寫實的情節,隱喻城市的現况和未來。故事寫法與張婉雯的風格相異,但核心議題彼此連結,同樣處理時代的人事變幻,關注弱勢者,只是選擇的呈現方式不同。
在虛構小說的另一面,韓麗珠亦不時在facebook寫她和家貓「白果」的相處,不少都收錄在日後出版的散文集《回家》「貓」的章節裏,她曾憶述用社交平台貼文的起始:「最初我只是寫我兩隻灰色的貓,因為我很喜愛牠們。」白果在去年10月離世,韓麗珠在專欄中記下最後的告別式:「領養貓時,牠已成年,按下貓的火化鍵,則像展開,從此我們有一種新的連結」。
■延伸閱讀
韓麗珠和謝曉虹同被視為超現實風格的作家,曾合著《雙城辭典》,其前身是文學雜誌的專欄,用一題兩寫的方式,構建相異又互通的神秘城市。其中一期以「啞」為主題,二人分別交出〈啞穴〉和〈啞門〉,詳見下周二(3月4日)《星笈中文》。
文:韓祺疇
圖:韓祺疇、arthobbit@iStockphoto、資料圖片、網上圖片
(本網發表的作品若提出批評,旨在指出相關制度、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,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,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,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、不滿或敵意。)
[語文同樂 第758期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