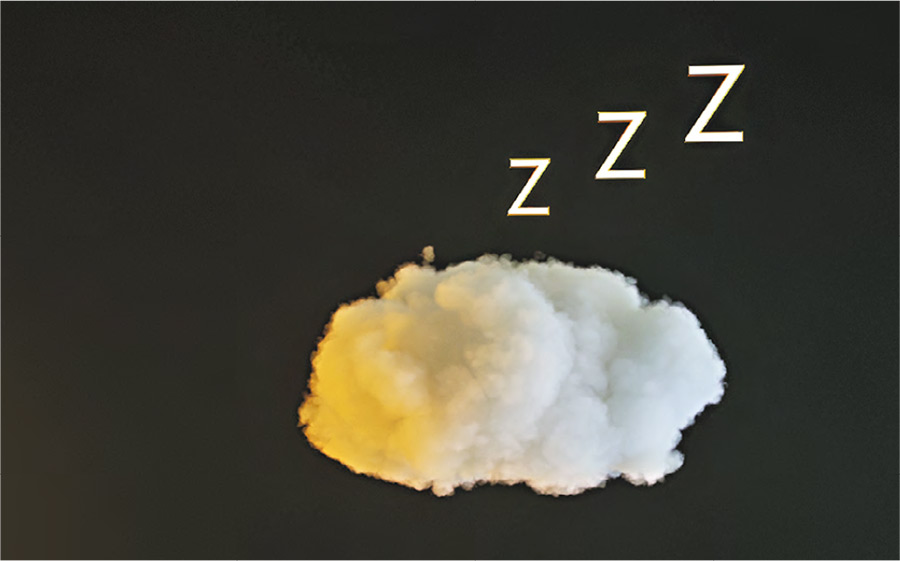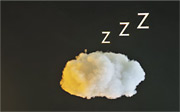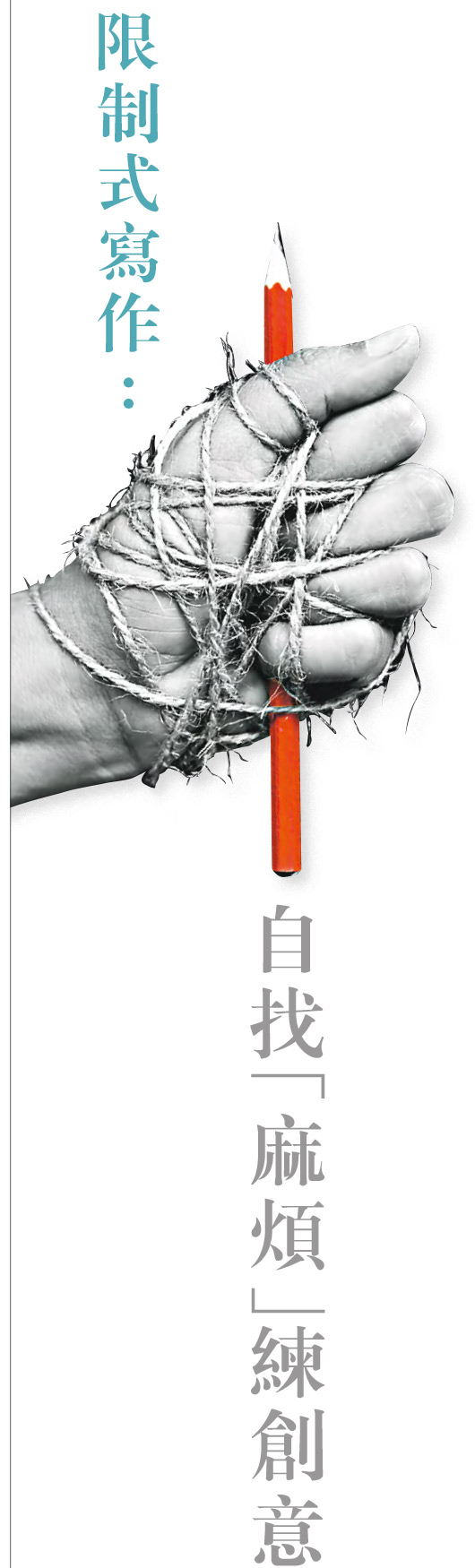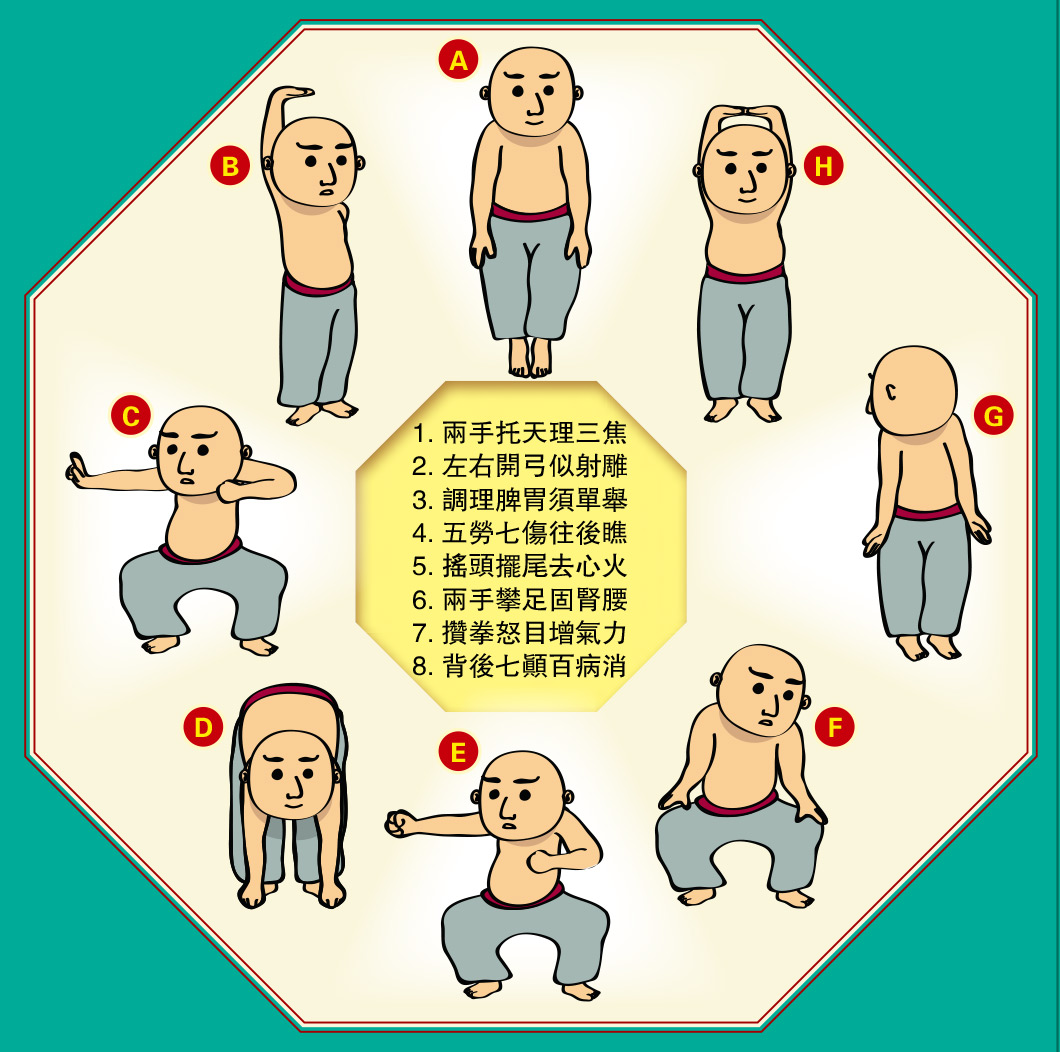生活關鍵詞:晝想夜夢……虛實相生……
【明報專訊】疲累的時候,我們放下活動的能力和清醒的意識,進入睡眠,然後在夢境中,獲得另一種想像的可能。夢境就如另一個和現實交纏,但又性質相反的世界,作為獨特的精神現象,古今中外,都不乏對夢的研究和分析。它可以僅僅是「日有所思,夜有所夢」的體現,也能是文人們想像死亡的方法,是生死間的狹縫;亦有可能,它就是現實本身。如果夢境足夠真實,我們要如何印證自己是夢是醒?
古人早已日有所思,夜有所夢
廣東話俗語「搵周公」,意指睡覺做夢,周公之所以和睡夢扯上關係,全因孔子一句:「甚矣!吾衰也。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。」孔子仰慕周公,沉浸周代典籍,時常夢見他,可惜年老時已經不再夢見周公。
早在春秋戰國時期,古人對做夢這種生理現象已有所覺察,甚至嘗試分析和理解夢境。據列禦寇所著的《列子•周穆王篇》記載,夢境分為正夢、噩夢、思夢、寤夢、喜夢、懼夢六種,即正常的夢、驚愕引致的夢、思慮引致的夢、白日所見之事形成的夢、喜悅引致的夢和恐懼引致的夢。這些皆是「神所交也」,即精神世界與外界交集而引起的,會因遇到不同事物,產生情緒而做不同的夢。
列子舉出「甚飽則夢與,甚饑則夢取」;「藉帶而寢,則夢蛇」;「將陰夢火,將疾夢食」等例子,指出飽腹時會夢見自己施予他人,飢餓時則夢見從別人處拿取東西;枕着腰帶入睡會夢見蛇;天氣即將變得陰冷會夢到火,即將生病時會夢到進食,說明人們會受身體狀况或外在環境的影響,而引發相關的夢境。最後得出「神遇為夢,形接為事。故晝想夜夢,神形所遇」的總結,精神遇見外界會產生夢,身體感官與萬物連接會產生事情,因此日有所思,夜有所夢,實為精神及身體感官,均與世界有所接觸而引致。列子在兩千多年前對「做夢」的分析推論,如今看來也相當合理,甚至可以說是頗符合科學解說。
■知多點
鄭人藏鹿夢
《列子•周穆王篇》中另載有八則討論人類精神狀况的寓言,其中一篇與做夢有關。文中提到鄭國有樵夫,砍柴期間遇見受驚的鹿,將之擊斃,藏於野外,打算之後再來取回。可是過了一會兒,他便遺忘了藏鹿之事,以為不過是夢境罷了。樵夫在路途上一直叨念這個「夢境」,途人聽見後,根據樵夫的「夢」找鹿,果真尋獲。途人回家後把事情告訴妻子,他覺得樵夫的夢竟然和真實一樣,十分奇怪。妻子則認為樵夫可能並不真實存在,一切不過是途人做的夢,連樵夫藏鹿的事也是他的夢境,現實找到鹿,也許是夢境成真。
樵夫對丟失鹿耿耿於懷,當天晚上,他竟夢到藏鹿的地方,以及拿走鹿的人。第二天,他根據夢境內容,找到途人的家,二人為爭奪鹿,告上官府。判官難以定奪哪些是夢,哪些是現實,最後只能判二人各得鹿一半。
這則寓言試圖探問夢境與真實間的界線,但同時也正好應合列子「日有所思,夜有所夢」的說法。無論是樵夫抑或途人,他們的夢皆是現實生活的反映。
醉生「夢死」思考人生意義
以夢為主題的文學作品,時常藉夢的特質探討真假虛實的分際,不過在六朝的志怪小說占夢或夢兆故事中,夢境往往是嫁接死亡的途徑,是生死之間擺盪的空間。有論者認為,六朝時社會動盪不安,戰禍頻仍,時人無從掌握自己的命運,這種無所適從的心態就在文學作品中傳達,尤其常用「夢」作為媒介,人物會在夢境中預視自己的死亡。如劉義慶《幽明錄》中記述的一則故事:曹操的謀士許攸夢見身穿黑衣的差役搬來漆黑的桌子,桌上放有六封文件,聲稱他明年七月會成為神明北斗君;然後又搬來一張桌,上面另有四封文件,稱陳康會擔任北斗的主簿(負責文書的官員)。果然「明年七月,二人同日而死」。故事透露了命定論的觀念,死亡預告應驗,人物似乎難逃命運的安排。
有人欣然接受死亡,亦有人嘗盡方法逃離死亡。東晉干寶《搜神記》中記顏畿病逝於大夫家中,家人把屍體迎接回鄉時,顏畿託引喪者傳話,告訴家人自己陽壽未盡,將會復活,只是服用太多藥物,傷及內臟,故不應將他下葬。顏畿的妻子、母親和其他家人陸續夢到他表示:「吾當復生,可急開棺」。唯獨父親不信鬼神之事,經顏畿弟弟游說終於開棺,發現顏畿「以手刮棺,指爪盡傷,然氣息甚微」,他的手指因不斷刮棺而受傷,尚有虛弱的呼吸。家人將他帶回家中照料,但他已經「不能言語,飲食所須,托之以夢」。如是十多年,顏畿最終還是衰弱至死。這則故事對死亡的態度更為悲觀,儘管主人翁多番託夢求生,結局仍不盡人意。然而,換個角度看,時人書寫、記錄死亡夢兆,反映他們對死亡的恐懼與抗拒,也可以視作對命運的一種反抗。
■延伸觀影
基斯杜化路蘭
《潛行凶間》質問現實本質
夢境也是西方電影的常見題材,其中鬼才導演基斯杜化路蘭(Christopher Nolan)編導的《潛行凶間》(Inception)曾掀起熱潮。電影講述盜夢者Cobb能夠潛入他人的夢境,偷取藏於潛意識裏的機密資訊。他和富商交易,透過夢境把「解散公司」的意念植入商業對手的潛意識。由於人腦習慣追索各種意念的源頭,植入一個沒有根據的外來意念非常困難,因此Cobb與團隊設計了多層的夢中夢中夢,打算逐步擊破對手的心理防線,建立新意念的根基,再將之植入。
導演精準捕捉到夢和潛意識的特性,把有關夢的各種概念,轉化成能夠承載故事的空間場景,將「人生如夢,夢如人生」的思想,以視覺方式呈現。電影角色異想天開的「入夢」任務固然緊張刺激,另一條敘事線亦相當動人:Cobb和妻子曾經一同遊歷夢境世界,一手一腳創建出整個城市,許諾攜手生活到老。可是妻子在夢中流連忘返,不願回到現實,他無奈下只能對妻子植入「這是夢,唯有死才可以回到現實」的想法。這個意念在她腦袋中慢慢生根,醒來後仍無法分清真實和夢境,最終從高樓一躍而下,企圖回到「現實」。
如果夢境美好,而且能夠完全由自己掌控,創建現實生活中無法擁有的一切,如此真實而夢幻,我們還需要現實嗎?堅持生活在「現實」的意義是什麼?現實和夢之間又有何區別?電影藉由夫妻的故事線,拋擲出連串問題,試圖透過夢,質問現實的本質。
文:呂穎彤
圖:Max Lirnyk、Deagreez、w-ings@iStockphoto;劇照
(本網發表的作品若提出批評,旨在指出相關制度、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,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,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,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、不滿或敵意。)
[語文同樂 第746期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