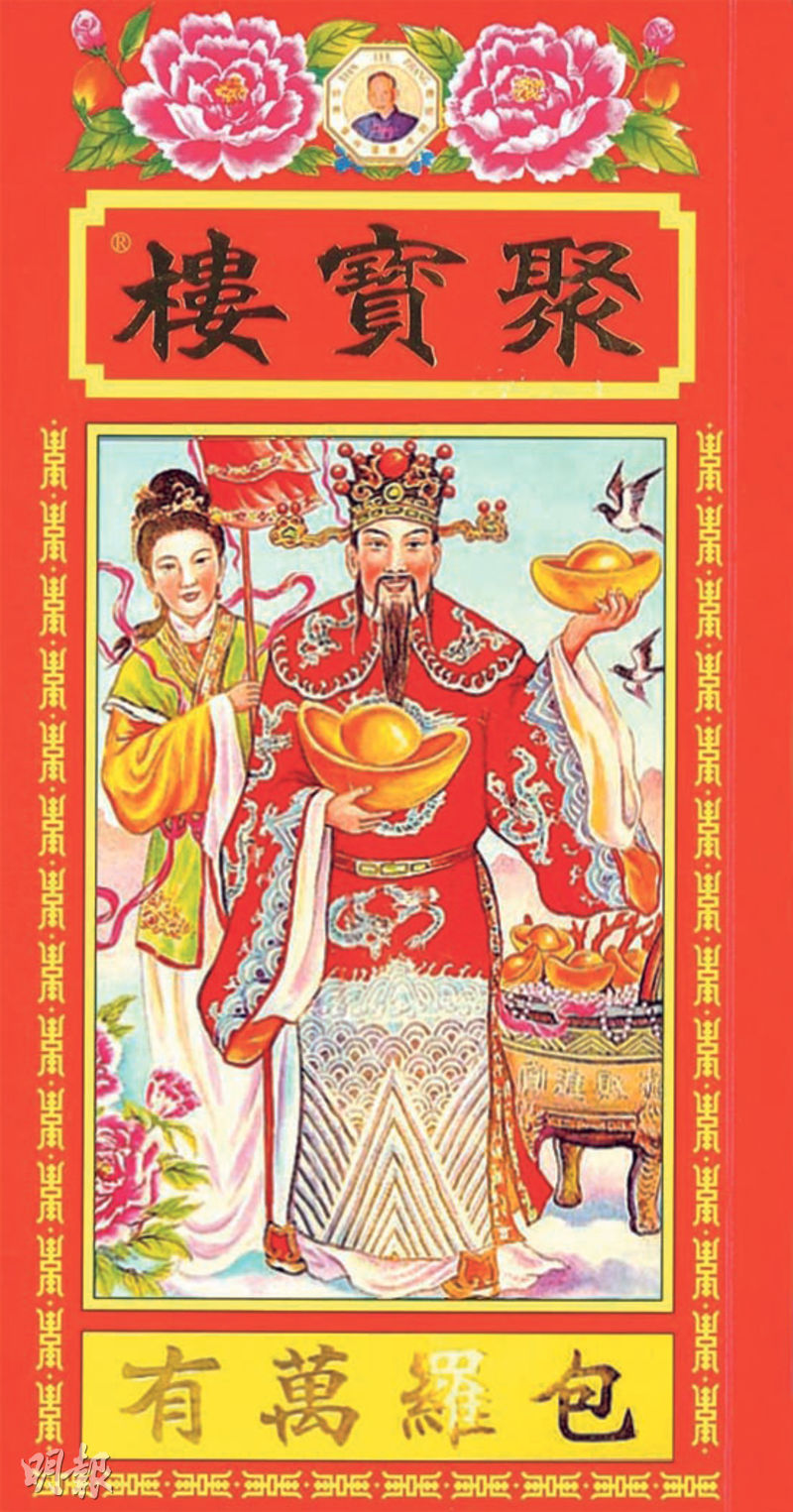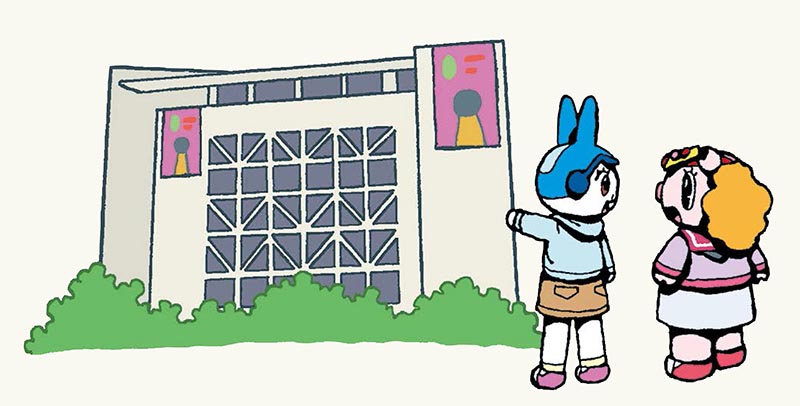視聽之娛:只凝視地獄之門外的偽樂園,也是一種奇觀?——《特權樂園》
【明報專訊】我們到主題樂園遊玩,是希望掃除日常的苦悶,暫忘現實的焦慮,欣賞驚人的奇觀,重拾愉快的回憶,享受身心的歡暢;而對歷史博物館、慘劇遺址、名人故居深感興趣,是想悼念無辜的消逝,了解過去的生活,汲取前人的教訓,保存時代的記憶,警惕崩壞的來臨。同樣是沉浸於現場實景的遊歷,一熱一冷,出發點截然相反,倘若成功給合兩者,自然是難忘的感官與思想衝擊。
樂園有幸福無血腥 更不寒而慄
祖納芬基里沙(Jonathan Glazer)自編自導的新片《特權樂園》(The Zone of Interest,2023)就是這樣不易消化的電影。故事不複雜,但需略為認識納粹德國的歷史——電影是奧斯威辛集中營指揮官赫斯(Rudolf H?ss)一家為主角的歷史想像。納粹德國在二戰期間實行「最終解決方案」,種族滅絕計劃下大量歐洲猶太人被屠殺。今位於波蘭南部的奧斯威辛,就是最惡名昭彰的集中營所在地,送進此處的猶太人被迫做極嚴苛的工作,然後被集體處決或進行慘無人道的人體實驗,喪命者逾百萬人。
這段歷史之殘酷與恐怖,不易為現代人想像,數十年來人類不斷回顧、悼念、反省,既不願悲劇重演,也欲探究何以會發生這種極惡的集體罪行。反思種族滅絕的電影不少,但如純粹強調集中營之恐怖,大聲譴責加害者,看似站在道德高地,不過是消費亡者,對認識歷史無甚幫助。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阿多諾(Theodore W. Adorno)曾言「奧斯威辛之後,寫詩是野蠻的」,生出滅絕暴行的文化無疑是野蠻的,一切譴責野蠻的文化產物包括詩歌,其實亦矛盾地使野蠻文化得到延續、流傳,未能真正批判;但後來他修正說法,痛苦的事固然應該表達,受折磨的人也有吶喊的權利。如何呈現集中營的暴行而又不令「揭露」淪為「奇觀」,創作者必須認真思索。
《特》中的赫斯一家,並非面目猙獰或外貌冰冷的典型反派,電影主要以他們在集中營旁邊的家園為敘事舞台,這座別墅也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「樂園」︰面積既大,明亮光鮮,家具擺設皆有品味;他們自建水池方便派對,也有園地蒔花養草,還有不敢造次的傭人使喚;附近既有資優校園讓小孩上學,同時有茵綠的鄉郊和清澈的溪流可供假日消閒。整齣電影聚焦赫斯一家的生活點滴,沒有任何一刻拍到別墅旁圍牆內的集中營情况,觀眾只能在他們的生活日常之中,聽見背景傳來不近不遠的槍決聲、呼喊聲,或看到營頂煙囪透出來的火光和燃燒屍體的黑煙。只有「幸福」的景象,沒有血腥鏡頭,卻更使人不寒而慄。
特權階級「惡的平庸性」
祖納芬基里沙想呈現的,是至今皆然的可怕現象︰許多特權階級、中產家庭,只擔憂柴米油鹽和工作升遷,明知體制在行惡,卻說服自己只是執行命令,盡忠守法,完全不關心他人的命運。政治哲學家鄂蘭(Hannah Arendt)曾深入探討人性「惡的平庸性」(banality of evil,過往常譯為「平庸之惡」,並不準確),以許多納粹黨人為例,他們絕非愚鈍盲從或嗜殺為樂,甚至在執行任務時展現精明的效率,但沒有意識到自己行為之惡,淪落淺浮,喪失思考能力。後來有研究指出,他們困於納粹反猶的意識形態,不管眼前現實為何,只奉國家和元首的想法、政策為絕對正確,這不單是恐懼違背命令的後果,而是內化了意識形態的影響。
那麼《特》能揭示這種「意識」的複雜性嗎?在使觀眾「細思極恐」方面,導演愈是將「樂園」拍得美滿空洞,無疑愈能突出可怕的浮淺。然而,完全避開大屠殺的畫面,又小心翼翼不欲令觀眾同情赫斯一家,在「情感」方面難以和觀眾聯繫(更遑論帶領觀眾反思現今世界各地的悲劇),只拍出「樂園」內各種平視、遠觀有如監視的鏡頭,事實上也是另一種「奇觀」。
若《特》是一部十來分鐘的短片,筆者會很佩服創作者的概念和執行能力,不過拍成長片,雖能激起討論,但深度欠奉,頗為可惜。延伸本文首段所討論的,參觀展館,除了知性的衝擊,也要有情感的連繫,又不能帶着遊覽樂園的心態,才是真正的歷史學習。電影實在應該跟《天堂無門》(Son of Saul,2015)對照看,後者完全以關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猶太人主觀視角出發,同樣不賣弄血腥,卻有種更教人不忍直視的可怕,當可補充《特》之蒼白。
■作者簡介
陳廣隆 - 中文教師,影評人,「香港粵語片研究會」及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」成員。著有《誰是金庸小說武功第一人?》。
文:陳廣隆
圖:安樂影片提供
(本刊刊出的文章若提出批評,旨在指出相關制度、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,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,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,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、不滿或敵意。)
[語文同樂 第695期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