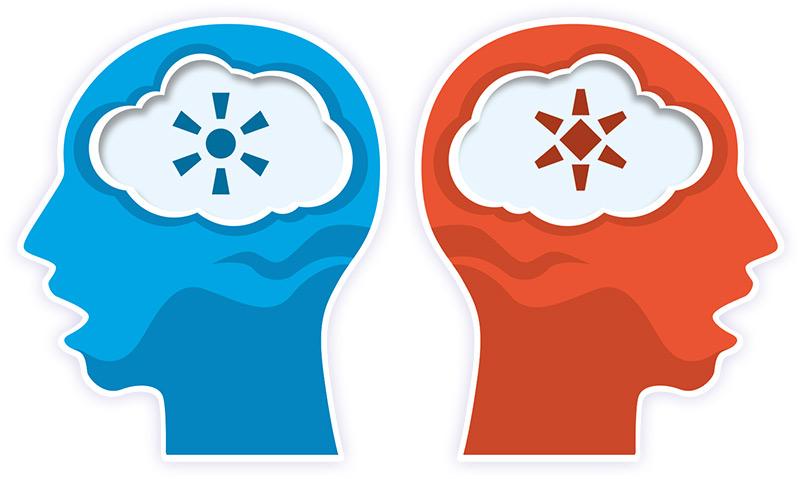潮看文史:民(man4) 信(seon3)
【明報專訊】前有蔡展鵬風波,後有高官飯局,娛樂性豐富的紀律部隊系統淪為百姓談資,政府則幽默地在未釋疑下叫公眾勿再深究,另一邊廂卻大談要讓不移民者有信心。在選舉幾乎不反映民意的年代,要求官員取信於民似乎不切實際;但求諸歷史,縱是人治的古代,民信(理論上)仍是重中之重。
治亂
大眾新近印象最深的,可能是宣誓安排不斷飄移,以及施政報告諮詢會出席者多由政府邀請而被批評假諮詢,與我們認知的「由亂轉治」迥異。古人認為立信是國家興盛的根本,不論重德的儒家把誠信放於生命之前(《論語.顏淵》:「自古皆有死,民無信不立」),還是重刑的法家強調賞罰分明(《韓非子.飾邪》:「賞罰敬信,民雖寡,強;賞罰無度,國雖大,兵弱」)皆然,禹湯開國而桀紂亡國即是「務信」與「背信」的結果(《荀子.彊國》)。最著名的史例自是商鞅變法徙木立信,打造秦國霸業基礎;王莽政策朝令夕改,本因民心所向而篡立的帝國遽成短命王朝。
強君
當然歷史上並非沒有強盛而不重信的時代。秦始皇不信功臣不親士民,隋文帝刻薄寡恩愛猜忌,政治依舊清明,一如韓非子所謂「人主之患在於信人」,國君應取信於民卻不能輕易信人以免掣肘,最終秦、隋速亡只因後繼者糟糕。但亦正因國祚短暫,反映出強勢國君的極限:縱使個人才能出眾穩住大局,若後繼者無法跟上腳步便土崩瓦解,更不用說失信的體制中利益團體轇轕,皇子傾軋本身就是一大禍端。最終收拾殘局的劉邦和李淵,基礎還是立信:約法三章/十二條廢除苛刑,軍隊對平民秋毫無犯,真正「由亂轉治」打造長命王朝。
民順
當百姓不再信任國君,民變湧現拖垮國家,是我們常常讀到的歷史教訓,唐太宗便常與臣下引用荀子的「水能載舟」時刻提醒要善待百姓。當然如此國君只是鳳毛麟角,隨着時代推移,監察百姓的制度愈趨嚴密,尤其宋代以後攙雜了軍事功能的保甲制下,鄰里受連坐威脅而互相監視以為制約,比之民信更要求民順,愈發遠離以民為本的傳統理想,以至明清盛世如永樂、康雍乾都被認為國富民貧頗有「水分」。但縱是監控帝國,明清還是不免因民變衰亡,民意的力量還是不能忽視——不過在現時主調下,明清之亡可能不再歸於民心問題,而是外力作祟罷。
■葉雨舟:書呆子一名,喜歡反思中日韓歷史文化的種種,希望東方社會能重拾對東方文化的認識。
文:葉雨舟
圖:資料圖片
[語文同樂 第527期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