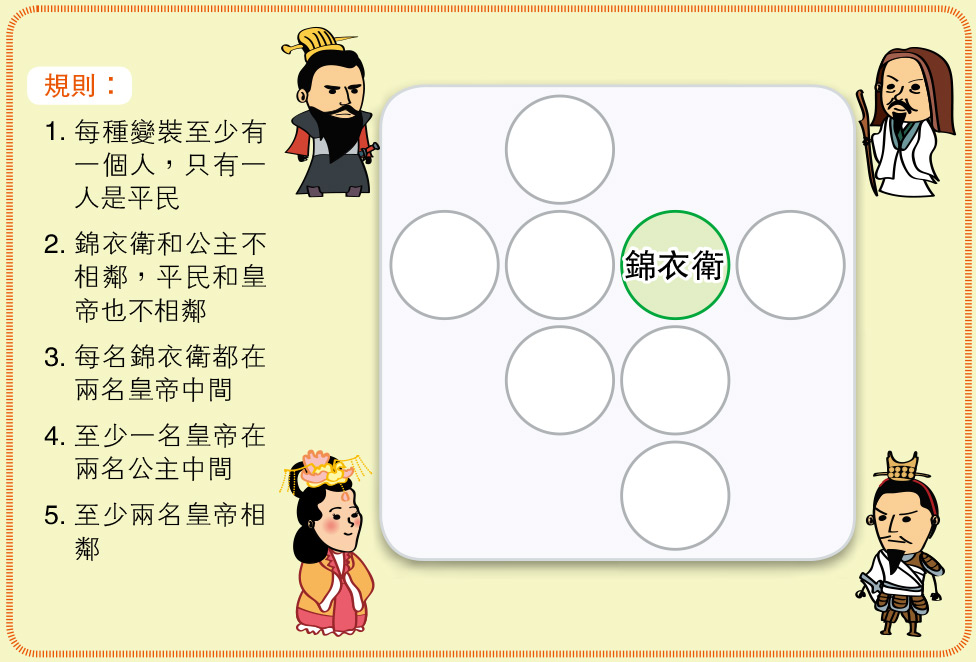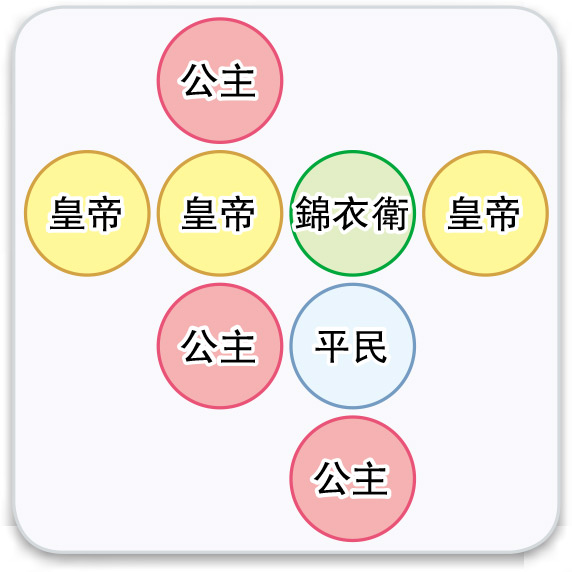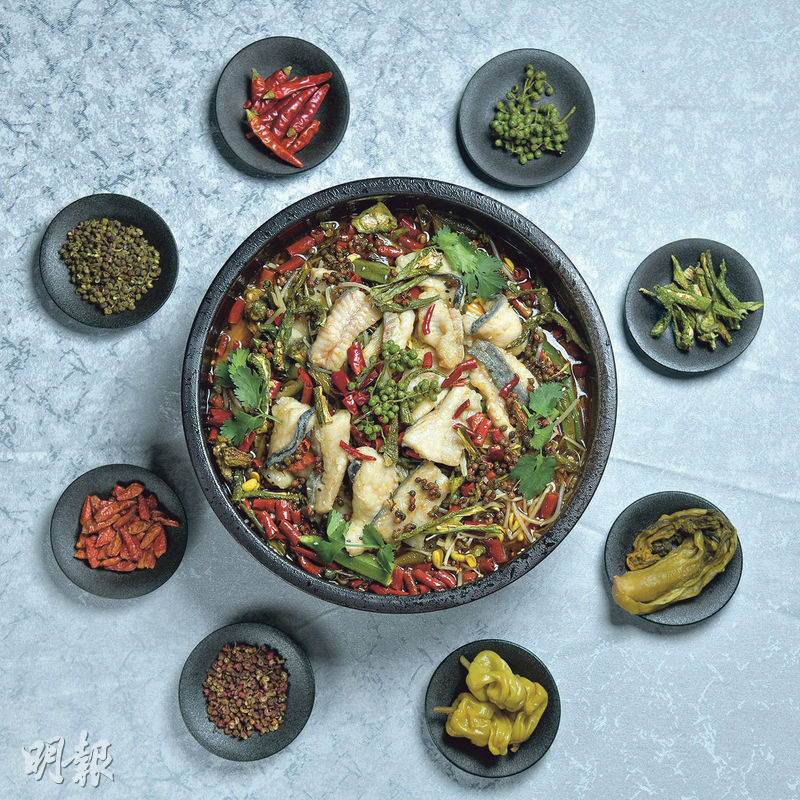書之異世界:四國遍路之後:尋找生命的步調
【明報專訊】柳宗元於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開首便寫道:「其隙也,則施施而行,漫漫而遊」,他仕途失意,被貶永州,但總算從昔日繁忙的公務中解放出來,讓他能放慢生命的步調並寄情山水,有足夠的空間藉老莊思想頓悟生命的真諦。而對於一切求快的香港人來說,又能否理解「慢」對於人生的價值?
香港的「快活」遊客
日本四國遍路朝聖之旅的7天行程完結後,解除了嚴苛的自我約束,從刻苦的修行者變回一般的遊客,一時間未能習慣,只知道內心渴望探索更多的地點。在未有仔細規劃下,我開始不按章法隨性而行。比如是大步危峽谷之行,最初本打算留宿一晚,但始終無法與該地擦出火花。由於不願浪費一分一秒,我當機立斷,即日下午便轉乘JR前往琴平,參拜傳說中日本人「一生必來一次」的金刀比羅宮。抵達時,很多遊客正從宮殿緩步離開,而我才匆忙踏上那接近700級的階梯。離開時,正猶豫是否在附近隨便找民宿休息,忽然發現乘搭琴平電鐵返回高松只需1小時,於是決定返回此次四國之行的起點。
翌日,在高松站附近的膠囊酒店醒來後,我立刻前往丸龜,並在當地以200日圓租了一輛單車。本來只想到丸龜城隨便打發時間,結果愈騎愈遠,意外地到了丸龜的地標「太助燈籠」,它背靠的便是坐落於丸龜港的京極大橋。巨型的青銅燈籠,與鮮藍色的圓拱鐵橋相映成趣。然而,更吸引眼球的並非美景。燈籠前,有個老翁把隨行物品紛雜地陳列在地上,感覺上是有意露宿此地。仔細一看,白衣、竹帽、金剛杖……不就是遍路行者的裝束嗎?
名古屋的「慢活」老翁
自從遍路之旅完結,我便沒有再穿上白衣和佩戴輪袈裟,但行囊一側仍掛着一支金剛杖。大概是憑藉這個「遍路」的共同標記,老翁在遠方高舉拳頭,彷彿要為我打氣。縱然趕着交還租來的單車,但這種不期而遇的驚喜,讓我忍不住走到老翁跟前,希望聽聽他的遍路故事。
原來老翁來自名古屋,他乘搭夜行巴士到達四國後便開始「逆打」(即以逆時針方向走四國遍路)。他跟一般「急行軍式」的遍路者不同,一般走完88所佛寺最快需要40天,而他走了只有四分之一的路程,卻用上了整整3個月!
我問老翁為何要走遍路,而且還花費那麼多時間。他只是簡單回答「good weather」和「good view」,似乎不像我將遍路視為苦行,而是純粹享受漫遊四國的歷程和風景。這種近乎奢侈的緩慢步調,或許才是遍路的本質。
生命的正確步調——
該快則快,能慢則慢
在加拿大傳媒工作者兼作家歐諾黑(Carl Honore)的《慢活》(In Praise of Slow)閱讀到英國詩人威廉古柏(William Cowper)的詩歌,甚為喜愛:
生命之潮不停迅速奔流
流過城市也許更加輕快
卻總不及鄉間河道風景
如此平和,一半清澈
我不禁反思,是否因為貪多務得,執著於用更少的時間做更多的事,反而錯過更多美好的事物與風光?其實在徒步遍路時早有啟示:所謂的修行,不止是完成既定目標。唯有在凡事求快的社會中,讓內心騰出空間接納不同步調,讓自己的生活該快則快,能慢則慢,才能讓自己擁抱生命的每一刻。
梁東源
中學中文科教師,背包遊重度患者。由於鍾愛日本的深山勝景而參拜四國遍路;為了挑戰「背包客的終極殿堂」而踏足北印度;疫後重新踏上征途,因朝聖古道而放眼歐洲大陸。期待在世界各地認識更多有故事的旅人
文:梁東源
圖:梁東源、網上圖片
(本網發表的作品若提出批評,旨在指出相關制度、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,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,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,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、不滿或敵意。)
[語文同樂 第756期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