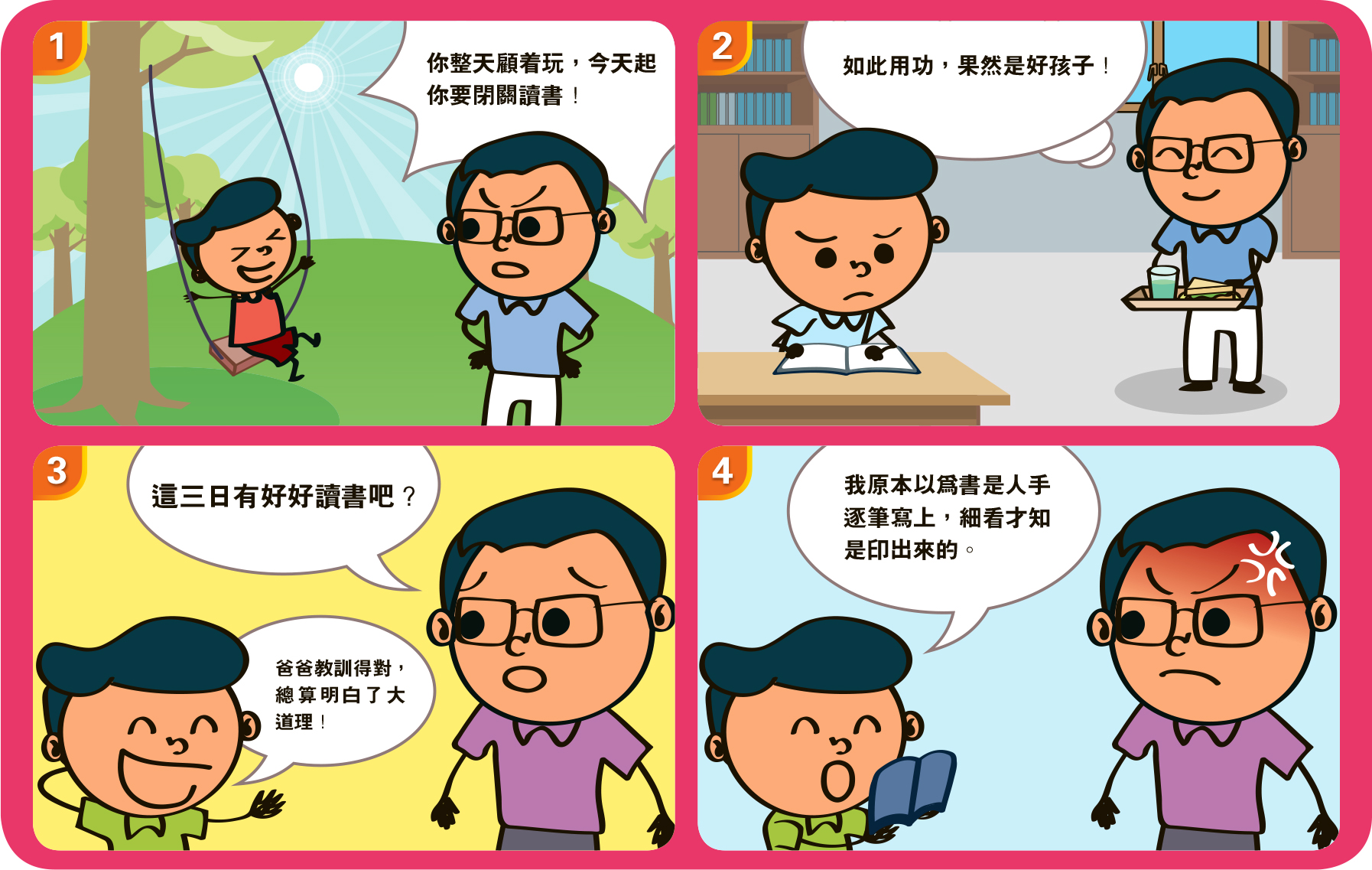語文小錦囊:愛狗的學者——季羨林
【明報專訊】各地各有風土民情,養狗的習慣也有別。著名學者季羨林愛狗,平常在街頭難以找到狗的蹤影,他直到前往尼泊爾首都兼最大城市加德滿都,終於看到心愛的狗。
■節錄
……我本來應該同這隻狗相依為命,互相安慰。但是,我必須離開故鄉,我又無法把牠帶走。離別時,我流着淚緊緊地摟住了牠,我遺棄了牠,真正受到良心的譴責。幾十年來,我經常想到這一隻狗,直到今天,我一想到牠,還會不自主地流下眼淚。我相信,我離開家以後,牠也絕不會離開我們的門口。牠的結局我簡直不忍想下去了。母親有靈,會從這一隻狗身上得到我這個兒子無法給她的慰藉吧。
從此,我愛天下一切狗。
但是我遷居大城市以後,看到了狗漸漸少起來了。最近多少年以來,北京根本不許養狗,狗簡直成了稀有動物,只有到動物園裏才能欣賞了。
我萬萬沒有想到,我到了加德滿都以後,一下飛機,在機場受到熱情友好的接待,汽車一駛離機場,駛入市內,在不算太寬敞的馬路兩旁就看到了大狗、小狗、黑狗、黃狗,在一群衣履比較隨便的小孩子們中間,搖尾乞食,低頭覓食。
這是一件小事,卻使我喜出望外:久未晤面的親愛的狗竟在萬里之外的異域會面了。
狗們大概完全不理解我的心情,牠們大概連辨別本國人和外國人的本領還沒有學到。我這裏一往情深,牠們卻漠然無動於衷,只是在那裏搖尾低頭,到處嗅着,想找到點什麼東西吃吃。
——節錄自季羨林〈加德滿都的狗〉
■學一學
對比
對比屬於修辭手法,把相反的觀念或事物對照比較,突出兩者的分別,令讀者留下更深的印象。對比有兩種運用方式,作者先寫北京不許養狗,他能看到狗的機會少之又少,下一段則寫在加德滿都受到狗「熱情友好的接待」,到處都是狗,穿插在孩子之間低頭覓食,以段落帶出兩地狗的對比。
另外,句子間也運用對比,「我這裏一往情深,牠們卻漠然無動於衷」,以自己對狗的「一往情深」與狗對他的「漠然無動於衷」對比,突出兩者不同的態度。
動物的代詞
文中的「牠」,指狗,是動物的代詞。在文中「牠」所指的可以是不同的狗,例如節錄首段的「牠」,代表作者在故鄉遺下的狗;尾段的「牠」則指作者在加德滿都遇到的狗。
■知多點
季羨林
季羡林(1911-2009)生於山東省,是著名梵文學家,也是少數懂中亞吐火羅文的學者。1930年他入讀清華大學,後於1935年前往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、巴利文、吐火羅文等古代語言。1946年回國,於北京大學創辦東方語言文學系,將梵文研究帶到中國。除了學術研究,他也出版多本散文集,包括《留德十年》、《牛棚雜憶》等。
(本網發表的作品若提出批評,旨在指出相關制度、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,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,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,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、不滿或敵意。)
[中華小學堂 第023期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