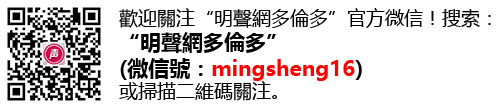《不虛此行》
文˙紅眼
胡歌飾演的故事主角聞善,畢業時都有做過作家夢,想成為電影編劇,可惜熬了幾年,同班同學都出道了,他卻被日子磨平鬥志,再寫不下去,也窮到幾乎連北京都住不下去,為了討活,唯有轉行替人寫悼文。當然,說得好聽是寫悼文,有個專業文類,直白一點就是做槍手,葬禮上的槍手。受人錢財,為人追思。電影唯美得多,沒我說得那麼髒。
《不虛此行》的故事正好讓我想起最近看過的兩部電影,一部是德國導演Christian Petzold的《盛夏餘燼》(Afire),另一部是中國新導演魏書鈞的《永安鎮故事集》。據Christian Petzold本人所說,《盛夏餘燼》是他前幾年確診Covid期間想到的故事,有點自嘲成分。年輕作家Leon正為他瀕臨難產的第二部長篇小說而煩惱,而且愈寫愈差,始終找不到一個寧靜的寫作環境修整作品,但其實是「我要成名」的自尊心作祟,讓Leon只看到自己的寫作才華,那才是寫不到好作品的真正原因。《永安鎮故事集》是另一個很有趣的後設作品,故事提到一支想要藝術商業兩得宜的電影團隊專程到永安鎮取材,籌拍名為《永安鎮故事集》的四個短篇故事,但這部電影其實只有三個短篇故事,而第三個故事就是關於編劇春雷不想為劇組妥協,違背自己的寫作原則,於是遲遲都寫不出第四個故事,甚至跟導演鬧翻。順帶一提,戲中飾演編劇春雷的演員,就是《永安鎮故事集》的真正編劇春雷。
這三部電影各自訴說了小說家、劇作家面對的三種困境。Leon是寫不好,寫得差;春雷是寫不出,不想寫;聞善是寫不下去。三個情况看似差不多,但其實有些分別,前兩個情况都是周期性的,如果創作者本身有寫作才華和恆心,捱過低潮之後就會恢復狀態。但第三個情况不同,寫不下去永遠是最致命的,就像《不虛此行》的主角聞善一樣,可能是際遇差、時勢差、環境差,更有可能是屢試屢敗,逐漸發現自己根本沒寫作才華,是寫作能力差。這就不是周期性了,像故事裏主角說得坦白,誰都會在自己追逐理想的第一幕以為人生有起承轉合,有其循環軌迹,但很多人的故事只去到漫長乏味的第二幕,而不會去到第三幕,也就是去到第二幕就已經完結。
放棄編劇 轉寫悼文
聞善放棄編劇志業,轉行替人寫悼文的原因也確是心酸。初時他自知不擅長描寫人物,為了成為一個好作家,寫有溫度的好作品,所以認真做實地調查,經常出入殯儀館,觀察人生百態,結果做不成編劇,閂了門卻開了小小一扇窗,反而讓他在殯儀館的轉介之下替人寫悼文。而且他這個槍手做得認真,不是依書照抄,而是似做記者,逝者已去,便透過親身採訪、聆聽親友講述的故事(也就是英文片名All Ears的意思),蒐集生平資料,推敲委託人不說、不知道的關於死者的那些破碎事情。既悲涼又荒誕的是,做不成編劇的聞善,卻在「悼文界」成為搶手貨,大家口耳相傳都知道他寫得好,委託人愈來愈多,甚至變成殯儀館的一條龍服務。
馬馬虎虎都算是以寫作養活自己,但收入其次,被人需要、證明自己的寫作能力,或者才是他安心轉行的最大原因。然而,寫作上的活着,是否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?拯救垂死的創作靈魂?「都是文字工作,還在寫就好。」當主角探望老師,老師就這樣安慰他,寫什麼都好,總之沒有放棄就好。其實都是老師的自我安慰,因為老師亦坦言自己在學院過得不好,跟他五十步笑百步。這一幕師生交談,倒又好像是《不虛此行》導演劉伽茵的一些自况,劉伽茵是北京電影學院出身,碩士畢業後便留校任教。雖然早在2005年憑自編自導自演的「家庭作業」長片《牛皮》在國際影壇嶄露頭角,幾年後再執導《牛皮 2》後沉寂十多年無以為繼,一直在電影學院執教。
是否「還在寫就好」?
《不虛此行》是個相當浪漫、美好的作家童話,男主角逐漸在別人的生死作業之中,獲得了繼續用心寫作的鼓勵。他不但有着令人羨慕的寫作執著和頑強意志,在他日漸孤獨自卑的生活之中,還有自己所創作的角色如幻影般默默陪伴,「就算只有一個人看到,都有意義」。故事勵志,明白是導演對自己創作低潮的一些感情投放,同樣陷入困頓的創作人或者會得到鼓舞,但現實比較殘酷,學院派的劉伽茵顯然對象牙塔以外的文字工作者,有着一些太美麗的想像。就說槍手這一種工作,實情並不是這樣浪漫,說得好聽,是為人代筆,其實十居八九收錢作假,鮮有故事裏的真情流露。
就是因為無感情、無感覺,委託者才打算用錢敷衍,悼文是,其他槍手文章亦是。用更俚俗的香港叫法,即是文妓。實際上這一步並不是那麼容易跨越,是要作出很大的妥協,不是退一步,而是退很大的一步,才能說服自己為死者家屬寫悼文都是故事創作的一種。當然,要把這樣的文字工作包裝成一個勵志故事可以很動聽,像香港都有執業法醫不斷出書演講,形容自己是替逝者說他們的故事,悼文則顯得更高雅了,甚至可說是為真正活過的人撰寫傳記,是真真正正的編劇。在我看來,所謂不虛此行的虛,是指心虛,要完全不心虛才是困難。
當然,並非只是做槍手才心虛。確實叫人往事翻滾,因為這些問題一直沒有離開過我,許多許多年前,網媒興起,當整個行業開始轉型,常疑惑炒稿追流量經營社交平台是否真的傳媒工作?又或者更多更多年之前,入行從事傳媒行業,掛着一張編輯記者證件,都算是文字工作吧,做着性質相似的事情,又是否仍然走在創作路上?那些隨着年紀大談藝文教育,投身藝術團體做行政職位的詩人作家們,又算是換一個形式繼續創作嗎?時至今日,類似的問題可能比《不虛此行》所感慨的更多、更不浪漫美好。譬如說,如果不再談論時事,寫寫社區保育與飲食男女,或者影視流行文化,是否真的「還在寫就好」?再無辦法在香港生活,搬到外國繼續創作,繼續用廣東話,寫香港故事,又是否同一種感覺?我明白,退而求其次,至少並不是選擇放棄,但是否代表繼續前進?前面是迎來轉變的第三幕,還是已經變成了另一部電影?
總有嘗試過退後一步,或者幾步,但要不虛始終艱難,都是有點心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