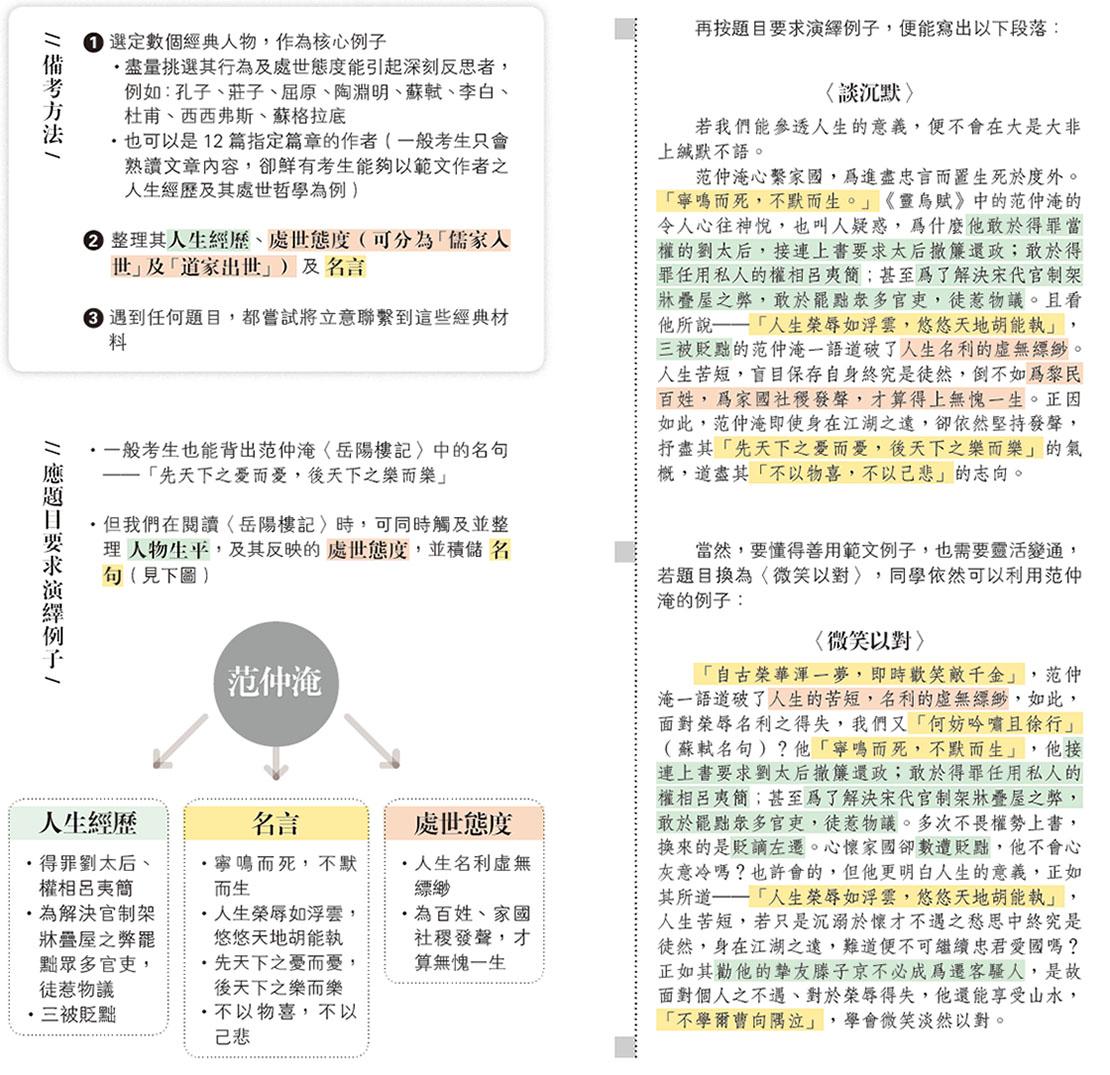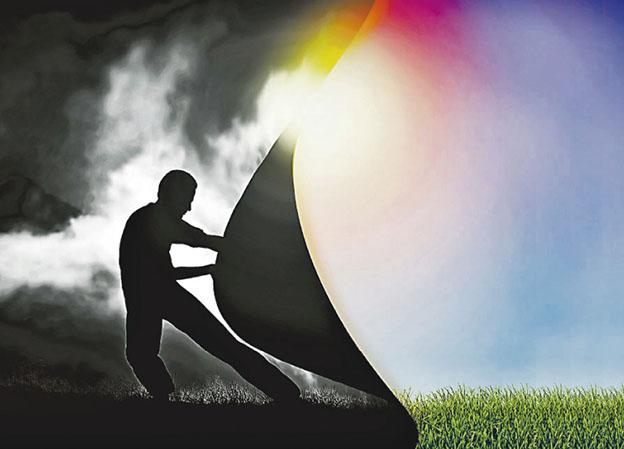言外言:孔乙己的「儒服」
【明報專訊】魯迅先生著名小說《孔乙己》中有一個「魯鎮」,那裏的酒店有兩類顧客:一是「穿長衫的」,可以坐在店內,要酒要菜,慢慢吃喝;一是「短衣幫」,只能靠櫃外站着,點四文錢一碗的酒喝。
而孔乙己,是「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」。為什麼呢?因為「長衫」是讀書人的標誌,不同於穿短衣的、大字不識一個的白丁。「長衫」就是孔乙己的「儒服」,是他的「知識分子身分證」,也是他最後的尊嚴,孔乙己就算窮愁潦倒,也比「短衣幫」要略高一等,所以他的長衫雖然「又髒又破,似乎十多年沒有補,也沒有洗」,但不能換,更不能丟棄。
「魯鎮」就是莊子所謂魯哀公時的魯國,孔乙己就是魯國的儒士。孔乙己似乎比魯國的「儒者」略好,不至於全無本事,他還有一點「道術」,「滿口之乎者也」,知道「回」字有四種寫法。
今天我們也依外表裝束,把人分為「白領(White-collar)」和「藍領(Blue-collar)」。「白領」相當於魯鎮的「長衫客」;「藍領」相當於魯鎮的「短衣幫」。我們依然「先敬羅衣後敬人」,覺得「白領」用腦「搵食」,懂的道理肯定比「食力」的「藍領」多。至於「白領」中有資格認證的,如會計、建築、法律、醫藥之「師」,高等學府博碩之「士」,普通民眾更由敬生畏,把他們的言論奉為圭臬,別說反駁,連質疑都不敢。殊不知「師」、「士」的「白領」,也是「儒服」的一種,不見得比孔乙己又髒又破的「長衫」更好。
莊子說:「有其道者,未必為其服也;為其服者,未必知其道也。」然而,從兩千多年前的魯國、一百多年前的「魯鎮」,到今天的社會,沒有多少人理會,我們仍相信「儒服」。
[語文同樂 第461期]